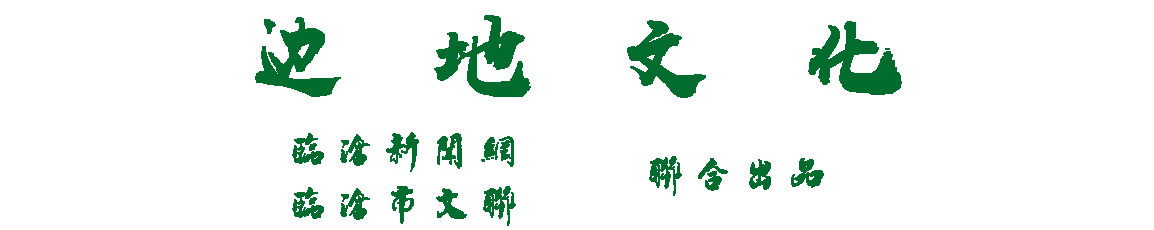
面对废墟时,内心的荒芜冷清恰恰与废墟本身完成了契合、平衡,并最终融为一体。那是一个荒芜与冷清的场,这次我进入的废墟,所给我呈现出来的便是这样,我也意识到废墟并不只是给人以荒芜与冷清。但这个废墟会让人意识到内在强烈的孤独感,你会再次感受到内部的废墟。这时,我是一个孤立的人。内在的孤独感。这样的孤独感,一直伴随着我们,让我们莫名忧伤,莫名慌乱,有时我们无法安宁,有时我们甚至会有孤独会影响个人命运,或者孤独是个人命运的一部分的感觉。其实,我们无法说出一个群体的孤独,以及一个群体的命运,我只能强烈感觉到内心的那种孤独。
废墟:在那个可以放映幻灯片的世界里,有人想看看自己拍的那些优美的风景,一些在茅草丛中探出来的马的目光,还有牛的目光,还有羊的目光,几个熟睡的孩子,一些河流,一些繁茂的杂草,还有其他在面对着它们之时会不由赞叹那是童话一般的照片。那是我,或者是别人拍下来的照片。那是我,或者是别人想再次看看那些照片。如果在幻灯片里,看到的依然是这些景象的话,我们早有心理准备,我们也将与任何废墟扯不上关系,但在那个略显幽暗的空间里,那个童话世界消失了,那个现实世界消失了,消失得让我或者是别人猝不及防,也让我或者别人大失所望,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一片废墟,而更让我或者别人感到不可思议和诡异的是,让我们在心理上有着强烈拒斥意味的是废墟之上出现了一些尸体,更多动物的尸体,一些血污的出现,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在那片废墟上发生了难以启齿的暴力,那可以说是一次暴力之上的暴力(废墟也可以说曾遭受过一些暴力,而在幻灯片里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发生着的暴力)。在黑暗的世界之中,我或者别人颤抖着关掉了投影机,我或者别人都无法说清为何会出现这样诡异的一幕。
那时废墟的存在就是一首诗。我突然觉得自己心目中的那首诗,就这样具象化地出现在了面前。这样的表述多少有些可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无法说出自己理想中的那首诗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但似乎无需纠结于此。废墟将是一首不长的诗,也可能是一首长诗,具有史诗性质的长诗,这首诗里有着我对世界一切诗意的想象。精神与思想将在其中缓缓舒展开来,我将感受到的不再是与个人,以及与他人之间的神经兮兮的心理与精神上的搏斗。有着一些我所希望的语境,一些我所希望能够承载的语境,但我也深知,对于废墟的感觉太过复杂,废墟之上无法容纳所有的语境。那时废墟给了我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历史,时间,政治,个人,命运,人性。这些感觉并没有先入为主所具有的弊端,它们就那样如植物般生长开来,就那样在我面前近乎有序地排列着,而与这些相对的应该是无序的,应该是芜杂的。废墟开始给了我无尽的诗意想象的空间,这才是最主要的。有些废墟,直视它们,或者用别的姿态面对着它们,它们就会有着让人诧异的诗性化的东西。我往往只是采撷其中的一小点,就已经满足。众多的废墟,被我解读着,很多时候,可能是被我过度解读,那时,废墟成了只属于我的废墟。被过度解读的废墟与被过度解读的世界。废墟,也是一个世界(似乎这样的解释的出现就是败笔)。我们随时在过度解读一些东西(似乎这样牵强的说法,同样也是败笔)。
废墟:流放的人。在名为西伯利亚,还是其他无名的地方。把时间都放在冬日里。寒流正侵蚀着那些或是有名或是无名的世界。一些被流放的人,一些自我流放的人。他们面对着的是时而具象化,时而抽象的废墟。他们在那些废墟面前,把自己所有的感觉打开,他们感受到了饥饿,食物的匮乏带来的饥饿,精神的匮乏带来的饥饿,在冬日的冰冷之中,他们蜷缩着肉身与灵魂,那时他们所希望的竟是有一小口烈酒能暖暖心窝。有着诸多流放的原因。他们在废墟上面看到自己。他们也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废墟。他们成了一具又一具废墟。他们生活其中的建筑,正遭受着残酷的生存环境的侵吞活剥,如果他们从其中离开,建筑在失去了人气托载之后,就会立即变成废墟。有时,人气只能暂时地起着作用。他们看到大地本身的荒凉的同时,也看到了建在大地之上的那些建筑的荒凉,以及自身在那个荒凉世界之中内心的虚空感与荒凉感。一群流放的人,往往很难把那些笼罩在大地之上的荒凉感驱除,反而是自身命运在那里起了一些作用之后,让荒凉感变得更为浓烈。流放的群体在相互望着,那时他们各自舔舐着干裂的嘴唇,那时各自眼里都只剩下废墟,他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空洞的眼眶背后的一个又一个灵魂,卑微的灵魂,猥琐的灵魂,高尚的灵魂,伟大的灵魂,无奈的灵魂,绝望的灵魂,以及充满希望的灵魂。这时,那些眼前存在的废墟于他们而言的作用,我无法说清,也无法进行任意的猜测。废墟在面对着那些种类繁多的灵魂时,似乎更需要隐藏起来。废墟,隐藏起来了吗?似乎废墟并没有隐藏起来,似乎那些废墟在雨雪交杂的世界里,变得更加醒目,这时的废墟成了白色的废墟,如白色城堡一般的废墟,这时的废墟不再是那些绿意葱茏的世界里绿色的废墟,生长着的废墟了。这时,有些灵魂进入了白色的废墟之中,成了白色的灵魂,有些灵魂在进入白色的废墟之后,成了绿色的灵魂,成了正在生长着的灵魂。一群被流放的人,以及废墟,白茫茫的世界之内,废墟消失,但我们依然清晰地看到那些正瑟瑟发抖的躯体与灵魂。
任何一座城市里人的生存现状,一种更多是挣扎着生存的图景(这时,我们往往生活在底层,为生活奔波),某个孤独的人就这样出现了。在夜里,当我在夜色中出现之时,恰巧可能与他相遇,他一脸慌乱,精神紧张,感觉如果那时我不小心挡着他,他就会暴怒,他可能就会做出让人吃惊的事情。我感觉有时候的自己与他是一样的,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心灵深处的废墟,以及这片废墟所曾遭受到的拉拽拖曳,我们都成了慌乱的个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适应那些喧闹的场,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与别人之间的关系。在认真观察之后,才发现如我们这样的人还很多,我们这些人可以形成一个群体,一个孤独的群体,一群在废墟之上游走的群体,我们很多时候是失魂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忘了自己的,我们同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汇入如洪流般的世界之中。我感到庆幸的竟然是与那个人之间保持了距离,但我依然能看到暴怒的他,在那个狭窄的世界里如熊般冲撞往前,不知道他所要面对的将是怎样的现实,他可能最终真正成为了一头熊。孤独的意义。孤独的意义在那时就是如何轻易地毁掉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被毁掉了,这我无法肯定,我内心里面的恶之花也暂时没有怒放,我与他萍水相逢,我也希望更多的人不会那般窘迫,不会如我那时一般窘迫。
废墟:在某个咖啡馆(准确来讲应该是酒馆里,咖啡馆里的人们在谈论存在主义,在讨论现象学,而酒馆里似乎很难像在咖啡馆里一样,优雅地谈论存在主义),我们变得不再优雅,我们在酒精因子的作用下,激烈地谈论着废墟,谈论着我们在废墟之中的生存状态。准确来说,我们并没有在酒馆里,我们就在某个废墟面前,意识到了存在主义,意识到了废墟的存在。废墟就在那里,我们的谈论将在很长时间里围绕着那片废墟展开。我们竟谈论到了一个人在坠落过程中所对尊严的依赖,如果没有对于尊严的依赖,我们的下坠将只是如任何一个普通东西的自由落体运动。光线变暗,我们无论进入咖啡馆,还是酒馆,抑或是废墟(某个废墟可能曾经起咖啡馆,也可能是酒馆,还可能是其他,有些废墟在失去了基本功用之后,我们已经很难回忆起废墟原来的功能),在那个多虑的思想中,总会有一些情绪的交杂,那时情绪失去了抒情性。废墟之中,竟有着一些纸张和思想的分子在弥漫,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嗅了一下,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我们在感受到淡淡的气息之后,才深深吸了一口,并突然意识到那种四溢和变得强烈的芳香。这时废墟成了我们在其中谈论的世界,我们谈论的东西偶尔才会跟废墟有关,那时废墟既可以被忽略,也往往无法被忽略,作为外部世界存在的废墟,对我们的心理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废墟变得不可或缺。有时是平庸的幽暗,有时也是平庸的明亮。我们在废墟之中情不自禁地谈起了思想的重量。思想的重量,我们谈论着那些我们更多时候不熟悉,或者是被我们误读的思想家与哲学家,我们还在更长时间里,谈起了我所喜欢又不是很熟悉的存在主义。
一个又一个废墟。当我对它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之时,我所看重或在意的是废墟所阐释(废墟在这个文本中,同样在一些时间里,具有着无比浓烈的象征意味和隐喻意)的东西,像这时废墟所在阐释的是孤独且被孤独所困,废墟所对于孤独的理解。最能阐释孤独的应该就是废墟。但这样的说法被我说出来之后,马上被我所推翻,最能阐释孤独的应该还是孤独的生命。只是在面对着那个废墟时,我竟没有先想到生命,而是想到了废墟作为一个贮存器,一个容器,所能容纳的孤独。我所想到更多的是孤独,废墟在成为废墟的过程中,以及所遭受的遗弃过程中,里面所蔓延和渗透的孤独感尤为强烈和浓厚。
废墟:变得越来越不真实的废墟,一个又一个裂痕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又一个砖头断落,一只又一只寒鸦栖落,在面对着这样的废墟之时,内心里面在一些时间里所追寻的东西变得有些漫长而虚无,但我也深知眼前的废墟只是呈现一种真实而已,似乎这才是真正的废墟的真实。在眼前的这个废墟之上,我所感受到的是在走向某个深渊,但生活所一直处于的非常态,也让我坦然面对着这些时常会出现的深渊。你无法抑制内心里面的那种慌乱感,你也无法抑制属于个体的对于废墟的认识,你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避开废墟,你甚至到处找寻废墟,你觉得很多废墟并不能只以简单的“废墟”就能囊括。生活的非常态,我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废墟前面,也可以算是生活非常态的一部分。只是在一些时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样而已。但我必须适应生活的非常态。在多次面对着生活的非常态之后,我还是有了一些心理准备,准备着随时面对着那些生活常态之下的非常态。
出现在废墟的那些诡异人物,一些对废墟异常着迷的摄影师和艺术家,让人感到美丽又让人不安的东西。摄影师和别的门类的艺术家,出现在一个废墟前面,并努力与废墟之间建立一些联系,有些废墟给了那些艺术家创造的能力与力量。我在面对着废墟时,我在艺术创造上同样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似乎废墟也给了我一种创新的能力,一种创造的能力。我们正用心灵建起一些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废墟。那应该是属于我们心灵的废墟,更多时候抽象化的东西。当我们意识到有着废墟存在的时候,废墟真成了没有任何生命意义的废墟。废墟与美学。只是美学上面的意义吗?似乎于我而言,废墟不只是具有这样的意义。废墟的一些东西如水迹般慢慢洇开,如花,如木,如鸟,如鱼,像一切,又不像一切。我开始把自己置入更多的废墟之中,是一次又一次有意的放置,以及一次又一次有意的在精神方面的放逐。废墟忽大忽小,但与大小无关,有时候的大是那种可以被人忽略的大,而有些时候的小却是无法被人轻易所忽视的小。废墟的大小区别不是很大。只是废墟。拍摄废墟。与记录废墟的一种方式。以及废墟的意义。废墟所具有的时间上的意义,以及美学上的意义。我们正从时间的蛛丝马迹中找寻着废墟所曾在美学上留下来的蛛丝马迹。我开始有了写作废墟的不可抑制的渴望。我在内心里面重新定义着“废墟”。“废墟”更多成了我的废墟。发现废墟之下的东西。众多的废墟需要重建,至少那些心灵的废墟是需要不断去重建的,只是我们感觉到了重建过程的艰难,艰难到足以让原来的废墟变得更是废墟。这个文本中的废墟,有时候是具象化的废墟,有时候就是抽象化的废墟,有时就是二者相互重叠之后的繁衍与庞生。
废墟:老唱片。想起了老唱片的声音。把我们带回到怀旧的情绪之中。那些老唱片存放在蜘蛛网之下很长时间了,蛛网一般的小角落。在又一个被我认为应该是“废墟”(很可能是象征意,有时我就这样沉浸在象征意的世界里,我喜欢那种在真实与不真实之间徘徊的感觉,“废墟”在这个文本中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载体,但我也深知在这个文本里出现的世界多少携带着“废墟”的特点与象征意)的世界里,一个老人用一个早应该被淘汰,至少早成为一个古董的老唱机(这里要形容一下它,一个灰头土脸已经失去了清晰意味的物件,发出声音之后,用声音再次确定了自己的存在,我就是在那些带着点潮湿和发霉的味道里意识到那个古老物件的存在,而老人被我长时间忽略。当我把目光转向唱片机时,我才发现了老人的手,一双颤抖的手,一双颤抖的手背后可能有着很多东西,可能有着多次让内心颤抖惊惧的经历,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时间,时间与历史,时间与社会,时间与人性,时间的厚度让一切有关时间与老人的东西变得模糊混沌),唱片机发出了喑哑忧郁的声音。老人与唱片机。老人只是在那里喃喃自语,我根本无法从蠕动的口中分辨出任何东西,他的情绪也是我无法把控的,这时我遇到了麻烦,如果我是想真正认识眼前的这个人,那还没开始接触就已经宣告了我的失败,我竟有了一种颓丧的挫败感。老人朝我望了一眼之后就不再望向我,我知道他在拒绝我,就像那个老唱片机所发出的声音,同样是在对我的一种抗拒,那些声音与现实有些格格不入,老人与现实有些格格不入。现实就这样不断改变着我。
一群人,这时一群人共同存在于那个世界之中,但这群人之间很难生活融洽,他们经常会歇斯底里地为一些小事争吵,他们会蜷缩于一些角落之中,把自己孤立起来,他们再次成为一个又一个孤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就像相互看到的都是遥远的星辰,遥远的星辰之间的距离与对视,每个人都把内心隐藏起来,主要是为了隐藏内心的荒漠,但人们又往往无法真正把自己隐藏起来。这时他们有意识地去找寻着那些已经作为废墟的建筑,那时他们成功把自己隐藏在废墟之中。在冬日的废墟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瑟瑟发抖,他们陆续从废墟之中走出来,他们无法忍受冬日里的废墟的冰冷,那是渗透骨髓的冰冷。
废墟:废墟之中生活着一群病人。废墟之中所生活着的那群病态的人,他们确实是病态的,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这与众多因忙碌因自负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病态与内心深处的焦虑是一样的。个体的有意义,个体的无意义。
面对废墟之时,便是想拥有一种无比独特,又疏离的体验。一种强烈的沉默。一种把自己放置于内心。各种各样的体验与感觉。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体验与感觉,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听着那段名为“绿松石”的音乐,里面不断重复着的咏唱时,我就感觉是在走入某片废墟,荒凉的废墟,寂寥无人,只有嗜血的鹰在山谷盘旋,空谷之中被遗忘的废墟,面对遗忘,那时候的悲伤与凄凉感便是我在听到这段音乐时的感觉,这段音乐真有一种强烈的带入感,我知道自己没有真正理解这段音乐,我只是凭借着直觉阐释着音乐,以及音乐所应出现的世界,那时虽然只有风,只有枯草在风中瑟瑟发抖的声音,鹰飞翔的声音,我没有听见,单调的声音,悲凉感就出来了。音乐里的废墟就这样出现。音乐与废墟。
废墟:音乐之中的废墟。音乐并没有停止。音符里夹杂着嘶嘶响着的风,在风声中更容易感受到废墟的存在。在音乐中,似乎要艰难些,但当风成为音乐的一个重要部分时,我们就会相对容易感知到废墟的存在。音乐,纯音乐,调子多少有些忧伤。我们总感觉废墟就在一个空谷之中。空谷之中的废墟,有鹰在叫(这是能听得到的声音,也是在那段音乐中,出现了好几次,而在现实中的经验在告诉我,其实要听到鹰叫还是比较困难,我们看得最多的其实还是鹰在空中静默地翱翔着),还有黄沙(能听得到沙子在风的作用下击打着废墟墙体的声音,但那是有着不一样的击打的声响,我们只需要细细分辨着就能听到貌似一样的击打声音中的不同,我们这时能肯定的是不同的墙体,或者是墙体的不同部分在遭受着来自风沙的碰撞击打),还有其他的声音,毕竟音乐首先是声音的艺术。狂烈的风沙总有一天会把废墟彻底吞去,这是我们能在音乐的悲凉之中所能感受得到的。音乐的戛然而止,似乎就是那个有点抽象的废墟的最终结局,也似乎就是很多废墟的最终结局。
斑驳的墙面上有着蜗牛留下的痕迹,还有着壁虎留下的痕迹,其实我是在那时候看见了爬行着的蜗牛,也看到了那个较之蜗牛爬行速度异常快的壁虎在墙体上行走着,壁虎真如履平地。我呆呆地望着蜗牛和壁虎,在看着墙面上的斑驳,至少一些斑驳是蜗牛和壁虎留下的。它们似乎并不在意所处的环境。它们可能也更钟情于眼前的世界。我感觉到了与眼前世界之间的格格不入,我无法融入眼前的世界,那时我只想快速地从那个世界中脱身。多少人将会有着如我一般的感觉,又有多少人会像蜗牛与壁虎一样坦然,那应该是坦然(那时我只能以我的角度来认识那些生命,这也是太多时候,我对很多生命所陷入的一种惯性认识),壁虎继续如我一开始所见到的那样爬行着,有时会倏然停住,似乎是把目光对准了我,它的目光里面的浑黄与迷离,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的对视竟也没有多少意义,这多少会让人感到有些沮丧。我所一直期望的与生命之间的那种对视,并没有在那个废墟的内部发生,这竟然是一种多少会让脊背发凉的对视,我总觉得它看穿了我,它看到了我那一直想掩藏起来的那些肮脏的想法。这时,我竟没有快速逃离废墟的冲动,而是看着壁虎静静地贴在了墙上一会之后,才迅速消失。停止到消失的转换快得让我有些回不过神。
废墟:废墟不只是破碎的瓦砾,以及瓦砾之上重新生长出来的萋萋芳草,也不只是里面偶尔散发出来的刺鼻的铁锈味,还有很多。那些废墟似乎是在以它们的方式,完成对于同质化世界的反抗。在这个文本中不断被重复,已经被过度重复的“废墟”是一样的吗?它们之间是不一样的,我在选择这些废墟时,是已经经过了一次过滤,是经过了多次多重的选择,只是难免还是造成表象和表达的重复。在面对着不知道该如何表达那些似乎一样的经验时,我们真是感受到了一些乏力与沮丧。似乎我们心目中的废墟就应该是一样的,且应该是被我们简化的,其实一个又一个的废墟的堆积,是一种复杂的繁衍,是与简化完全相悖的。我一直想抗拒的就是同质化。同质化对于艺术的伤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眼前至少不只是一个废墟,或者是一个大的废墟,大废墟之下被细化的几个小废墟,有些是建筑,但那是不同的建筑,那是不同建筑所呈现出来的对于“废墟”的不同注解。在“废墟”面前,似乎最适合谈论暴力,毕竟很多废墟就是暴力的产物,暴力如熊熊燃烧的火,暴力如钝拙的刀,刀把世界粗暴地留下了更多时候悲剧的空空如也的不完整的外壳。貌似的一个空壳,一个空间,一个废墟的空间。如何把自己放入那个空间的架构里,我竟有一种渴望进入那片空间的层层纹理中的冲动与渴望。一种空间,然后自己应该在那个空间的什么位置?我开始想确定自己在那个世界之中的位置。我们有些时间里都想确认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有时我们甚至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世界的中心。而废墟的坍塌,是让自己彻底无法找寻到自己的位置。由废墟所构建的空间。不真实的国度,不可思议,思想被带入另外一个世界,灵魂在另外一个世界中成了另外一个灵魂。“复杂性,远去的空间感”。
黑暗之中,扑鼻的黑色粉末,那时一切是黑色的恶,里面可能有着一片黑色的废墟,如果黑暗一直持续(黑暗似乎没有要消散的而感觉与迹象),我在想黑暗里真有一片废墟的话,里面将会囤积了多少被废弃,多少无用的东西。一些人会在暗处囤积了很多无用的东西,他们继续囤积着那些东西。在黑暗中,我也将无法厘清废墟的真实。废墟姑且是存在于那片黑暗之中。废墟并没有存在于那片黑暗之中,当亮光出现,一切是完整的世界,而没有任何废墟的痕迹。其实那里应该是有一片废墟才是,我能嗅到废墟的气息。碎片,无法聚集在一起,也没有人会去有意把它们聚集在一起,无疑这是遭受了野蛮的力量的冲击之后,所形成所留下的碎片。精神会破裂成类似的碎片,当有这样的念想时,我竟会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竟清晰地感觉到了内心图景的碎裂。孤独之书。由碎片由孤独的个体组成的精神之书。由囤积的那些或是有用或是无用的碎片组成的精神之书。那些与孤独对抗的艺术家,那些成为孤独的一部分,或者是孤独成为他们一部分的艺术家,他们身处的世界里所散发出来的有关孤独的强烈的铁锈味,思考孤独、感受孤独并表达孤独,他们创造力的延展与作品的特异,异常强烈。孤独制造了某些艺术,以及如艺术般的人生。一些人在自己周围竖起高墙。一些人内心的图景,内心的冲突,有关孤独的繁复感受,更多是一些不断被扯成碎片的感受。孤独感的深重、潮湿与发霉,孤独感所带来的毁灭性,那些看不见的菌斑渗入孤独。那些潜藏在日常生活内部的孤独,那些无处不在的孤独。一些怪异的人群。城市中生活着的孤独的人群,属于个人的孤独,属于城市的孤独,属于时代的孤独。有些孤独为失去、流离或偏见而生。有些孤独为艺术而生,有些孤独因偏见、妒忌而生。
废墟:一个在这之前不停与废墟相遇时,都不曾有过的感觉。自己在那个空间之内行走之后,我惊异地发现眼前的废墟与在这之前,我所见到的那些废墟所给人的不一样的感觉,主要是源自废墟之上的那些乌鸦。这些乌鸦的出现,而且它们暂时是静物,与废墟一样是静物。在这之后,它们同样会飞离废墟,往往只是暂时地飞离,但现在我所关注的是它们成为废墟一部分时,所对我产生的冲击。乌鸦,总会让我感觉从它们身上能窥见灵魂的孤独。乌鸦是孤独的,当它们与废墟发生联系之时,这样的想法是我们无法避开的。那时这是多么强烈的感觉,那时我同样窥见了自我灵魂的孤独,那时我便是一只乌鸦,至少是如乌鸦一般,我们都与废墟之间发生了联系。总会觉得眼前的乌鸦时一种超现实的鸟。废墟之上的乌鸦,我脑海中瞬间蹦出来的是深濑昌久镜头下的乌鸦。灵魂的表达。灵魂的自由表达。灵魂的有些压抑的表达。内心的孤独、焦躁与动荡不安,真实的鸦,孤独的鸦,铺天盖地的鸦,更多群居的鸦,那些暗夜之中明亮的双眼,浓烈的工业废气中飞翔的鸦……深濑昌久更多在摄影中表达着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在很长时间里的一些状态。深濑昌久在与妻子离婚那段时间的心境,让他持续关注乌鸦在世界中的表达。那些更多是孤独的鸦。深濑昌久亦是其中的一只,特别是那些在摄影中以单数以孤独出现的乌鸦,就应该是他。在提到乌鸦时,我已经无法绕开深濑昌久,我无法忽视废墟之中的我,亦是长时间因为一些原因而孤独,而焦躁不安。
把目光投向废墟。探索者。探索者的时代。什么样的时代才是探索者的时代?探索的目光正在慢慢被一些同质化的眼光和经验所消磨。众多的废墟被忽略。它们的存在似乎只是除了暗示人一种过去时间的存在。而在探索者眼中,废墟绝对不是这样简单,也不能这样简单,这时我想成为的就是这样的探索者。我想探索的似乎就是时间赋予一个场域的不同形体。像美的不同表达方式。像内心在面对着废墟时的些微变化。我把目光投向废墟,那时我忽略了废墟旁边的大河,我也忽略了有人正在走往那个废墟的路上。我早已出现在了那里。我不能说早已预谋,但至少我早已计划出现在那里。废墟之上,一片沉寂,即便那个匆匆赶来的人,来到那片废墟时,只会加重那片废墟的沉寂。没有任何的生命。生命似乎不属于废墟,至少是不属于那片废墟。那是我把目光有意投向废墟之后,所发现的,那段时间,我出现在任何地方,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内心的渴求就是废墟,像极了很多时候内心对于孤独的渴望。废墟在我看来至少是孤独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孤独的一个较为形象具体的,很多时候,孤独并不具体。
废墟:那些更多是由孤独及其所制造的废墟。环形废墟。内部的废墟。在不停行走过程中,会遇见众多的废墟。由时光所制造的废墟。由时间进入空间所制造的废墟。那些废墟往往会引起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唏嘘不已。说是我们在感叹废墟本身,还不如说是我们在为自己唏嘘。看到一些废墟时,我总会不可避免地把现实中的废墟与驻扎在内部的众多废墟进行对比。有时感觉自己的内部就是一个废墟。我观望着这个废墟。许多人内部驻扎着的废墟。许多人观望着这个废墟。那种面对任何一个废墟时的忧伤与感叹出现。真实的废墟,见到了太多真实的废墟,然后真实的废墟变成抽象的。那时我一个人出现在一片桤木树下,那是我第一次强烈感觉到了孤独,桤木树上是静默着的乌鸦,它的漆黑特别醒目。我已经忘了那次出现在那个世界的真实原因,可能我就只是想来到那里闲逛一下,也可能有着一些很明确的目的,来看一看那片桤木林。桤木数量很多,很难找到一棵躯干笔直的树,我面前的那些树木躯干往往虬曲且疙瘩满布。对于一种树木的偏见便由此开始。偏见是在多年以后对桤木有了一些更多的了解时才消失。当偏见消失,我再次回到原来我出现的那里,这次我的目的很明确,我就是为了一片桤木林而来,但是出现在那里之后,我都不敢相信眼前出现的,放眼望去,一棵桤木都没有了,别的一棵大树都没有了。我不知道眼前的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是偏见所带来的狭隘与可怕蚕食了那些桤木?这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属于一棵古木的孤独。我们都有着属于自我不一样的孤独。可能我感觉错了,毕竟一棵桤木都不存在了,但总觉得他们的孤独还在那个世界里蔓延着,漫溢开来,漫溢到了我的身上,我开始在那个世界里为了一片曾经长得繁茂的桤木林而伤感。我只能在回忆中回到那个时间和空间,只是我的往回走举步维艰,往回走的渴望越发强烈,那个时间和空间竟变得越发荒漠化。回忆中出现了一个人,那时我在一片坟地里,暮色正慢慢降临,我是在猛然抬头时看到了那个人从某个坟墓前走下来。首先冒出来的是,那个人一定是从哪个坟墓里走了出来。毛孔紧缩,脊背发凉,那样的感觉在那之后的一些时间里,经常会再次出现。那些源自灵魂深处的孤独,所给人带来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我想从那片坟地里遁逃,只是我遁逃的速度并没能把那个人甩掉,他出现在了我面前。我终于看清了他。只是我不敢相信他会出现在那里。他问我有没有看到他的媳妇,他说他的媳妇去摘一些桤木的叶子,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了,只是她迟迟没有回来,他担心她会不会在那片繁茂的桤木林走丢。人是可能在那片繁密的桤木林里走失的。我只能如实说并没有看到,他说他要问问我的马和牛,他说马和牛也说没有见到她,他说他还要再去找找,他媳妇一定是走失了,只是因为暮色降临的原因,老眼昏花的媳妇找不到从树林中走出来的路。我还是没有从惊惧中走出来。当我回到家跟母亲说起这事时,母亲惊诧地说那个人的媳妇,不是已经离世了一段时间。母亲说出这话后,她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她把我紧紧地抱了一会。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那种惊惧中走出来的,抑或是那样的惊惧一直如影随形,只是在一些时间里,它才会闪现,而另外一些时间里,它沉睡着。沉睡着的惊惧,在眼前的荒漠面前,再度苏醒。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前眼前的荒漠,就像我经常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荒漠化的内部世界一样。有那么一刻,我的回忆竟变得有些清晰起来,我猛然意识到还有那么一棵桤木。那是一棵神树,我们在来那片坟地祭拜祖先时,我们先要从那棵桤木祭拜起,先是神树,然后才是逝去的祖先。我来到神树前,神树还在,神树长得异常繁茂,那应该是我见过长得最繁茂的一棵桤木了。离开桤木,暂时不再沉浸于回忆的窠臼之中,一些时候,回忆会带来很多问题,一些我们现在困扰其中,并不知道如如何解决的问题。原来桤木林所在的地方,现在都是田地,没有种什么庄稼的田地,那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废墟了。一定会有人这样感叹,没了桤木林的地方就是一片废墟,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再次在那里种植出一片桤木林,更何况我们从未种植过一棵桤木,我们只知道把它们连根拔起,做成一些根雕。离开那片桤木林,我的想象力开始发生一些作用,刚才还无法回忆起来的那片桤木林,再次出现在了面前,我看着它们从眼前慢慢消失,其实那样的时间并没有丝毫的慢,我看到了桤木林消失的速度之快,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有时我们就一棵又一棵桤木,不是像极了桤木,而是就是桤木。自己是桤木这样强烈的感觉,在那些辗转奔波之中,在被强烈的孤独感所困扰的过程中感觉尤为强烈。
我出现在了那个边境上的小镇,落寞,荒凉,据他们说,这里曾经喧闹非凡,曾经繁华过,繁华景象超出了你的想象,从这些已经几乎成为废墟的建筑上很难看到。废墟之上的那些民族依然穿着自己的服饰,依然讲着自己民族的语言,依然跟我们讲着一口口音很重的汉话,他们让我感到很亲切,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有一会,我暂时不去关注小镇的建筑与在里面蔓延的气息,我与那些人进行一些交谈。我们的交谈所围绕着的其实只是生活的碰撞,他们与小镇对面的人群之间的碰撞,以及正在发生着的与我们之间的碰撞,他们要面对着很多如我们一般的人,他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可能早已在内心鄙夷过我们对于他们对于那个小镇的莫名阐释。那个小镇还没有显现出废墟的特点(其实我早已模糊了对于废墟的认识,我也无数次诘问自己,废墟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也无法说出,其实我总觉得对于废墟的定义并不是我理想之中的定义,更何况一定义就有些把视域变狭隘了,而狭隘并不是我所希望的)。离开小镇,没过多少天,我就忘了街道,我就忘了里面隐隐透露出来的颓败气息,但我记住了在小镇上流淌着的有着强烈异域气息的音乐。那些音乐一直存在于那个世界,我总是有着这样的感觉。我不懂那个世界的语言,那时特别强调和考验感觉,感觉是最为重要的。但我知道自己的感觉在这之前就已经变得有些钝拙,我只能依靠着那些已经不是很敏锐的感觉,在感觉着眼前的世界。那些音乐里面,开始出现了一些浓烈的忧伤感。其实在那个小镇,我看到了一个有关废墟的展览。是梦中还是真实?应该是真实的,毕竟它在我记忆中显得那般真实。
废墟:一个有关废墟的展览。里面有着各种废墟风画、照片、雕塑以及实物。那是我能想到的一个最为完整的有关废墟艺术的展示。展览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开展,但观看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小镇上的人们很多都出现在其中,他们就想去看看真实的废墟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让他们感到最吃惊的是展览里面展出了小镇的照片,并配了这样的文字:可能的废墟,可能我们都身处在废墟,废墟不只是小镇,还可能是我们个人。在见到这些文字时,人们是倍感震惊的,这个配文虽然有着强烈的警醒意味,但似乎又有着强烈的某种亵渎的意味,虽然这是一个经历繁华之后变得稍微有些冷清的角落,但怎么能与废墟扯上关系,或者最多与废墟扯上关系的只能是眼前这个显得有些突兀的有关废墟的展览。每一个人都在那个照片前驻足停留,那无疑会在人们内心留下一些阴影的文字,一些挥之不去的阴影在笼罩,但我们也有强烈的感觉,那些照片至少是在述说着一种可能的真实,至少我们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可能会成为废墟。如果不是小镇照片的存在,那其他的有关废墟的事物中的一些竟有着惊人之美,有时甚至会让我们忘记自己面对着的是与废墟有关的一切(近乎一切),我们竟只会有面对着美的强烈感觉。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在黑暗中摸索着。黑暗中的摸索,只能凭借着手指对于物的棱角的感知来认知世界,这样的认知方式是我所感兴趣的。那些往往存在于幽暗的环境之中的废墟(即便很多时候,废墟是处于一个明亮的世界里,但我依然感知到废墟的表象上,显露出来的由里往外渗的幽暗),我只能更多发挥触觉的作用,我触摸着废墟的一层又一层的纹理。我所会触摸到的东西是无法预料的,这真的就像是发生在黑暗世界里的摸索,一切不可预见,一切出乎意料。我在黑暗中感觉到了废墟本身所携带着文化意味,以及如生命一般释放出来的生命意味。我继续在黑暗中摸索着,除了在废墟之内,我还出现在别的环境中,只是为了不会让摸索的脚步停下来。在黑暗中的废墟里行走着着时,脑海里浮现的是“流浪的陌生人”。有时我们就是一个又一个在大地上流浪的陌生人。我们心中常怀着某片大地。而现在我心中怀着的是废墟,种类繁多的废墟,真实的废墟,想象的废墟,存在与不存在的废墟,心中同样有着各种各样对于废墟的认识。我从一片又一片废墟之上,找到了那些让心灵有所寄托的东西,我的心灵也变得不再那么虚空,废墟在填充着一个又一个虚空的灵魂,废墟也在改变着我们对于内心对于灵魂的认识。我们被流放,我们的精神遭受着某种程度的流放。我们都是流浪者,我们在一个又一个颓败正面临着消亡的废墟上,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身上以及灵魂深处所具有的流浪者特质。我们不断在流浪,同样我们也希望找到一处灵魂的故乡,让自己不再有着那种流浪的痛感。我们所面对的就是陌生的自己。在那些陌生的世界里,我们不断发现让自己倍感陌生和惊讶的自己,另外一个自我,另外的好几个自我。我们所在一个又一个废墟上面,收获的也是陌生的对于世界的认识。我总会觉得自己还一直处于流浪的路上,那种内心的踏实感有时候感觉到了,有时候又荡然无存。让我们认识到让自己都感到有点陌生的自己,是有点激动。我们在不断往朝陌生的自己纵深。这时候,废墟不在,这时可以换成与废墟不一样的任何世界,我们正在朝内心的道路不断往返着。这时,废墟再次出现,我又突然意识到废墟出现与存在的必要。
废墟:阳光,月光,清晨,暮色,植物的芳香,鸟兽的奔走,这些元素聚集在了那里,虽然它们出现的时间不一样,但它们中的几个元素的出现,便足以与那个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是先看清了那个世界,那个世界的真实,那个世界里蔓延着的这些足以虚化一些东西,造成一些错觉的元素。我们会随时遭受着这样的极具二元对立的冲击(或者不只是二元对立)。两种现实,或是多种现实。其中一些是我们需要顿一下才会相信的。我们往往只相信或者只希望某些现实。一片被遗弃的城堡。一片曾经的城市,或者至少是城市的局部,可能是华丽的璀璨的一部分,可能是常见的不显眼的。那样的局部,那样的城堡,曾经太过普遍,但只留下了一座,或者这座都只是一部分,已经是局部的局部,也是世界的不断被细化的一种。我只看到一个被遗弃的城堡的局部。已经没有守门人的城堡,已经没有人居住的城市,那时植物暂时沉睡,那时鸟兽躲在了暗处,那时只有阳光的毒辣,那时不是清晨,也不是暮色之中,那时也没有如水的月光的洒落,眼前的一切都是那般寥落与混乱。城堡中的卡夫卡已经离开。城堡中生活着的是一群漆黑的乌鸦,有那么一刻我竟误认为它们就是城堡中的卡夫卡。曾经的守门人卡夫卡离开了,他被离开城堡的汹涌人群所裹挟。我就那样行走着。
艺术的永恒性。在面对着众多艺术之时,我们都希望艺术的永恒与艺术性。艺术性总会被时间淘洗着。艺术的表达,艺术的永恒在那片废墟面前展现出了一种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肯定艺术必将是永恒的,我们只能肯定某些艺术应该是永恒的。在见到那个曾经本身就是艺术,且它的那些细部都是艺术的废墟,艺术的诸多形式,我脑海里瞬间出现的就是有关艺术的种种,那可以说是艺术所在我脑海中最直观的表达。眼前的那片废墟,就是由各种艺术的消亡与正在消亡所制造的。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艺术经历了怎样的劫难。艺术会在一些时间里,陷入到由粗暴无知所制造的高墙之内,艺术就在这样的高墙之内陷入一种尴尬,甚而是绝望的境地。我能感受到眼前的这些艺术所遭遇的尴尬,我还能肯定的是制造眼前的这些艺术的艺术家一直都默默无闻(可能曾经并不像现在这般沉默),在那些残存的碎片上,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那是一群默默无闻寂寂无声的艺术家,甚至在他们存活着的那个时代里,他们可能只是一些匠人,只是一些并没有被人重视的匠人。我在面对着那些残片时,我能肯定的是自己面对的是一些由真正的艺术家用时间与生命所制造的艺术形式。艺术之内,艺术的内涵也是可以被我进行无线解读都是不为过的,但在面对着这些残片时,我放弃了解读。
废墟:一个沉默的人出现在了那里。沉默者。他已经无法掩饰因痛苦而僵硬变形的脸。莫非他是还活着的那些艺术家之一。我出现在了他面前。面对着沉默时,我有点手足无措,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才更好打破沉默。他只是朝我望了望,就继续低着头去抚触其中一块残片。我一直以为那些被摧毁的艺术所存在的时间已经很长,而在面对着那样长且厚的时间的薄片与厚片时,他需要让所处的环境变得静默下来(那也是后来,与一个地方考古学者交谈时,我才意识到的,只有在那样的静默之中,他才能在残片中真正定义时间,而时间被真正确定对于他们而言,太重要了)。时间的错觉,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制造。在那个沉默的老人身上,我感觉到的也是时间带来的一种错觉,我有点不希望眼前的这个老人与眼前的这片废墟之间有着任何的联系(而真实的是老人与废墟确实是有了联系)。别的一些人出现在了那片废墟。那些人并没有表现出如老人一般的难过与沉默,我在他们口中得到了真实的信息,确实这个老人为数不多的还活在世上的曾经参与了那些艺术创作的人之一。有可能那个老人会在一些时间里,也会偷偷希冀那些创造的艺术能够流传的时间会长一些,至少自己不会看到它的消亡,而有点讽刺和让人感伤的竟是他亲眼目睹着创作的艺术作的消亡,而且还是彻底消亡,那些残片将会被一些人处理掉,那时这片废墟也将会被改造,废墟不再存在,如果废墟存在,可以算是一个艺术的场的祭奠,但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祭奠的场,这也可能是老人所感伤的其中之一,老人感伤竟没有一处可供祭奠那些正在死去的艺术的场。从那些残片上,从那些被加工过,同样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艺术形式上,也可以看到眼前的老人所曾经参与过的一场艺术上的革新。特别是那些在墙体上所进行的艺术上的革新,是多么不简单。眼前的老人,沉默者,以及那闪烁着探索光亮的艺术残片,感觉那应该是很突兀的,但现在他们正以某种方式完成了一次无奈的平衡。一个完整的墙体,有着各种艺术门类在上面的呈现,是各种艺术得以让那个墙体变得更完整。但在那一刻,我所看到的并不是完整的,我只能通过局部感受到某些局部的艺术的美感,以及所带来的震撼。即便是在细部,即便是一些残片,依然有着让人震撼的美感,以及对于美学的一种定义。我似乎喜欢定义,又似乎不喜欢定义。残片所组成的废墟。
沉默与语言。面对那个废墟时,只有沉默,只有静默。那一刻,竟然没有一丝风,竟然没有任何声响却破坏静默的世界。
废墟:诗人说那就是废墟一样的世界。如果站在远山之上来看这座城市的话,城市中的一些古老的建筑还是稍显突兀,这些建筑所呈现的是这里曾是以前某个王朝的都城,与现在的城市繁华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当诗人这样说之后,我暂时把那种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的时间越久越发感受到了内心的孤独感抛却,这是一座孤独的城市,主要是城市之内生活着众多的孤独的人。诗人说城市变大了,而一个人变得越发卑微了,但我暂时把这些随时意识到自我的这些感觉放在一边。我把注意力暂时放在了“废都”上,一切的时间以各种讲述的方式被讲述,而寥寥的建筑也在以建筑的方式讲述着一些东西,让我猛然一颤的是,无论是那个所谓的“废都”,还是曾经的一个都城,以及现在异常繁华喧闹的城市,它的背后是一座山,前面是一个高原湖泊。这时,我们早已没有继续把注意力拉回过往的意思。我们暂时把注意力放在了人生活在山与水之间,我们自己也是,暂时不去管那种孤独感。
某些力量的藏匿之地。这些力量藏于黑暗之中,力量之表就是疲于奔命的废墟之衣,而那些力量在沉睡多年之后可能会再次喷发,喷发出火,喷发出光,喷发出某些文字一般的力量,喷发出一些已经在那里遗失很久的精神。废墟之上,我们看到的竟是精神的昏聩与堕落带来的毁灭。那些思想的清洁性,那些有着与黑暗、迷狂、懦弱、麻木对抗的力量,竟然藏匿了起来,藏匿在了某片废墟之下,我们找到了废墟,我们还需要进入废墟,只是思想的清洁性以及思想的力量,在废墟之下已经携带上了一些戾气,已经有了一些蒙尘。废墟一如我来之初,只是静默,只是停留于颓丧的境地。
废墟:我们进入了那个据说暗藏了众多危险的思想的废墟,但进去之后,我们先是多少有些失落,思想的光芒已经无法穿透暗夜的浓烈,我们那时只觉得在浓稠的暗夜中,由于灰尘的原因,让我们有些喘不过气,当打火机点燃,但打火机不能长时间被点燃,而且打火机的亮度,也不足以把那个漆黑的空间完全照亮,在些微的光芒中,我们看到了那些墙体上面的艺术作品,在那些艺术品(已经变成残片,已经破损严重)上面,我们是隐隐能感觉到那些艺术,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蒙尘,但依然能释放出几丝明亮的光,艺术之光中的迷乱,艺术之光中的自由,以及对于纯净与美感的迷恋,都在其中得到了呈现。曾经的那种被展现,一定是让很多人内心为之一震,一定也是那种让人震撼让一些人觉得里面潜藏了一些危险的思想,毕竟那些艺术的形式中,有一些是异常怪异的,一些残体,一些血淋淋的残体,那能说是暴力美学吗?
找到一种声音,分辨着各种声音在嘈杂的场中的混杂,听声音的能力,在这时,显得尤为重要,忽视、过滤一些声音,显得尤为重要。心灵的另一面,只剩下心灵的另一面。我们在找寻着声音,我们还在努力分辨着音色。在一个废墟前,在一个又一个废墟前,我们听到了各种声音。有时竟会有很奇妙的感觉,我们想在废墟的裂缝间看到某种生命,这时壁虎发出了声音,那是很轻易就会被我们忽略的声音,但为了捕捉任何细节,即便我放弃了很多细节,即便我忽略了很多细节,但壁虎在墙体之上的游走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忽略的。壁虎倏然消失,与壁虎一起倏然消失的还有其他声音发出的声音,鸱鸮的声音消失,当意识到所听到的是鸱鸮的声音时,我眼前出现的是黑夜中鸱鸮的眼睛。
废墟:一些生命的乐园,像壁虎,像蟑螂,壁虎很少,但蟑螂的数量异常多。无论是壁虎还是蟑螂,所会给触觉带来的初始感竟惊人相似的,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二者之间的区别。在那个世界里,我们依然清晰分辨出二者的区别,我们也轻易分辨出各种生命的不一样。在那个世界里,似乎生命就应该以一种混沌的样子存在着,我们开始对它们有些误解,特别是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图谱稀少时。没有人出现在那个世界,也没有人对那些生命有丝毫的觊觎。平时很少有人出现,我如果不是因为对废墟的兴趣使然,我也绝对会把这个已经成为一些生命的意愿的破败之地遗忘,又是一个建筑,但建筑已经没有任何特点,它只是某户人家曾经的房屋。现在这家人早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他们下落不明,他们早已不再存在于我们很多人心里,可能还有那么一些人等待着他们回来,并让那些生命暂时从这个世界退出,但有时你无法确定壁虎的去留。
一个废墟里有着诗性想象的迂回。我把想象的能力交给了废墟,我总会有强烈的感觉:废墟给了想象一种依托和翅膀,想象不断向水一样漫延开来。那时我关注的不是废墟之后的故事,我关注的反而是废墟与诗性想象之间的联系,我喜欢诗性的想象所带来的空间感。我在那个空间里把废墟暂时遗忘,废墟是一种依托,是一种必不可少但又可以被暂时忽略的世界,废墟本身并不是多么宏大的空间,但那个现实里很小的空间感,却让我有了想象一个大的世界的可能。我突然发现废墟本身,就是一个迂回曲折的存在,我就是那样沿着这些迂回曲折的路径朝世界之内走去。诗性想象对于世界的重要,特别是对于我的重要,特别是对于我的现实的重要,在那一刻,我只有这样强烈的感觉。把人从那个世界里过滤,其实那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面对很多废墟时,我更希望是我一个人,我不希望很多人,特别是我的亲人,像我的女儿会对废墟产生阴影。诸多的废墟所在一个小孩眼里,将更多会带来夜夜的梦魇与疼痛,我听到了女儿在很多个夜晚的哭声,哭声之中所暗含的惧怕和担忧,让我感到揪心和疼痛。虽然我在面对更多废墟时,也是在不断找寻着那些美好的东西,以及它们所给我的对于美好的想象。我正通过不同的废墟认识各种各样的美。美感的多样性。美感所拥有的宽度与广度,这些都将是我去思考的。有些美给人的感觉是怪异的,那些让人不适的东西不断出现,这些所让我不适的东西竟是我最为看重的。那时我所感受到的是多种的风在那个世界里肆虐,风里还夹杂了一些冰凉的水珠,我的想象和感觉被风与水珠的姿态所吸引。
废墟:那里曾是一个牧场。这时,我无法控制脑海里浮现出某部电影。一个暴雨之夜,一个逃亡者救了农场中的一头新生的牛,如果没有逃亡者的出现,母牛是无法顺利产下那头小牛的。这时,其实已经有两个新生的生命,一个为了救赎的人,一个为了新生而在四处流浪的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这只是电影的开始,远远不是电影的结束。这部电影在那一刻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主要一个原因是,那曾是牧场的地方与电影中出现的农场的自然风光很相似,那时现实进入了一个虚构的电影,同时虚构要进入现实。虚构在映照现实。眼前留下的是曾经有过牧场的痕迹,至少在很短时间里,这些痕迹还不会消失。这个牧场背后是一些游牧的人,他们赶着羊群,他们还赶着牛和马。他们出现在了这里,每年总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会出现在这里。那时,他们的生活都与游牧有关,那是一年里有着太多生命诞生的时间,一切围绕着新生的生命展开,人们在新生的生命之上感受着让人极为感叹和激动的东西。那段时间,那个不是很固定的牧场很重要。而现在,在那个废弃的牧场上的一些痕迹在说明,它将会彻底被废弃,那些游牧的人已经不再游牧,我不知道在很多年的游牧之后的不游牧,所会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但没有人出现,只有从那个姑且算是废墟之一种的曾经的牧场上呼呼吹过的风。我总觉得那时,风似乎想带走一切。
思想的城邦被摧毁之后,思想开始被迫在大地上流浪,并在旷野中重新生长。旷野成了思想的居住地,以及思想的一种生长地。在世界流浪的思想,在那片旷野重新纷纷汇聚在了一起。我们成了流浪的人。流浪曾是我们所无法逃脱的命运。众多的生命为了生命的意义而到处流浪,而被迫到处流浪。个人的流浪,复数的流浪,我们很多人都回不到故乡。思想的流浪,因为复数的流浪人群而有了悲壮的意味,我的第三只眼睛看到了思想在让人绝望的广袤沙漠中流浪,思想的嘴唇干裂,思想缺少水的滋养补给,思想在混沌的感觉中看不到任何生命,如果沙漠是一种生命的话,思想看到了一种生命,仅此一种。一种生命,一种思想(那时思想正慢慢被消磨),二者的相遇是孤独的碰撞,最终依然还是孤独。沙漠最终把思想吞噬。沙漠所留下的只是沙漠,沙漠太过于厚重,它把思想的废墟彻底掩埋。我在那里看不到任何废墟,但我知道沙漠吞噬了众多的废墟,也吞噬了太多的思想,以及真实的自己。
废墟:想象中的废墟。一个想象中的地洞。人们在里面悄然隐身思考。光线努力抵达地洞,地洞之中的那些思考者,却极力避开那些已经变得柔弱的光,思考者所依靠的是黑暗,他们在黑暗中思考,在黑暗中,只有思考的光芒会穿透粘稠的黑暗在地洞中成形成影(在暗黑的地洞里没有任何影子形成的条件,而想象中的这个地洞之中,影子却让人吃惊地存在)。我低伏着身子,把耳朵靠近那个洞口,我听到了里面正在发生的(但也更可能是很久以前的只是一直在洞里萦绕激荡着的回声)激烈的争论声,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考,以及有着不同的思考方式,以及有着对于现实的不同认识,争论不休,我听到了争论不休。那些争论不休的声音所制造的场,让那个地洞显得并不怎么安静。那里应该是安静的,里面堆积了一些动物的尸骨,这是现实,里面还可能堆积了一些夭折的孩童的尸骨,这也是现实,我看到了一些人把夭折的孩童裹进一些碎布里面,然后把他们丢进了洞里,这时我才意识到只想象了一个地洞,而现实中却有着盘根错节的地洞,那些我所以为只会发生在想象中的很多争论竟在洞口发生里,虽然并没有发生在地洞之。想象中的地洞与现实中的地洞要有所区别,可以说想象中的地洞与现实中的地洞完全不一样。现实中的就在我面前的那些地洞,因为有了孩童的尸骨,而让人倍感一些恶念丛生,也让人倍感悲凉,那是命运之一种,孩童的夭折背后有着太多的东西,也有着让人在残忍中可供发挥和想象的空间,孩童的命运,孩童命运背后的人性,可以有着太多可供思考的东西。而想象中的地洞里,没有任何尸骨,也就没有孩童的,动物的,地洞里生活着一群人,他们在已经成为废墟的地洞里,用思考对抗着地洞成为废墟的速度。一群思考者,他们思考着现实中的一些失败者的命运与梦境,他们也思考着失败者的失败之路,这时他们猛然发现自己也是失败者,他们只是暂时藏身于此,毕竟外面的雨水依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这时,那个地洞,暂时存身的地洞成了失败者的宫殿。一群所谓失败者聚集的宫殿。其实那绝对不是宫殿。那里只有一些燃烧后的灰烬还在释放出一点点的光热,而那群失败者对那些微的光热的渴望。其中一些失败者携带着一些思想,其中一些人的思想不免有些尖刻、偏激,他们在那个依然算是思想的城邦里,谈论着自己成为一个失败者所在世界的洪流中到处流浪,他们的流浪不是为了思想的驻留地,毕竟你无法控制思考。他们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流浪。“流浪”可能并不准确,他们只是出现在了世界的很多个角落,同时从事着各种职业。其实,他们已经很少去谈论思想,他们只是不停地谈论着自己从事的职业,职业的卑微与生活的艰难。
破碎的文明残片,在面对一个又一个考古现场时,那个考古学家所感受到的便是如此。他是一个地方性考古学家,不知道这样定义他,他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更多时间里面对的都是地方性知识,但这样的面对并没有让他感到任何的沮丧,相反有时他竟还警惕地想让自己,不要太沉迷于对那些文化现场时间现场的过度迷恋。他们往往要出现在很多废墟之上,他们要不断进行挖掘,那时他们的身份既是考古学家,又不只是考古学家,他们会因为挖掘到一些珍贵的东西而激动,他们也会为没有什么收获而沮丧。其中一个考古学家,他挖开了第一层,第一层的东西与他所想象和预料的一样,然后是第二层,那个他基本可以确定时间的东西也如期出现,他因此而可以兴奋几天,也同样会因此而感到有些沮丧。作为考古学家的意义不止于此,这是他说的,他说考古如同人生,如果都仅仅只是按照预期在发生的话,很多意义将会悉数消失。这次他来到了某个废墟,考古队暂时把挖掘的范围,确定在了那个不是很大的废墟之上(当然考古所面对的不只是废墟,废墟只是其中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一部分,废墟在很多时候是表象也是内里,但也在一些时间里,废墟的内部是更深刻的时间,被挤压成固态一般的时间,是可以一目了然的时间。在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时间时却是无力的。坚硬的时间与柔软的时间。我无法说出对于两种不同形态的时间的感觉。考古学家很肯定自己对于坚固的时间的喜欢。一层又一层的时间,以及与时间相对应的一个又一个物件),考古学家们所面对的永远是未知数,他们所面对的永远是时间之谜,我不是考古学家,我只是更多与那个偏居一隅的地方考古学家简单谈论一下考古。现在这里的描述属于那个考古学家,而不是属于我,同时是属于他个人的,而不是属于所有考古学家的。他们就在那个小范围内谨小慎微地挖掘着,一些物件出现,一些大致的时间被确立,那些物件的价值基本被确定,但这一次让所有人都兴奋的事情马上将会发生,对于认知的干扰也将马上发生。考古学家挖掘到了一块古瓷片,只是一块,他们想象中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古老残片,并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再次确定了一下,只是一块没错,而且还不是一块完整的瓷片,有一些被切割过的痕迹,古瓷片的价值不菲,依然有收藏的价值(但是他们在面对着那块古瓷片时,所想到的并不是它的收藏价值,这也只能是考古学家所面对古老文物时心态之一种),当其中一人看到了那个切割过的痕迹时,所有人开始变得异常兴奋,他们能肯定的是可能会在正在挖掘的地方发现另外一半,也可能会在别处发现另外一半。寻找另外一半古瓷片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那是经过了多年以后,他们在离那个废墟几十公里的一片废墟里挖掘到了另外一半,当他们把两块古瓷片放在一起后,它们缝合在了一起。他们在两块(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一块)瓷片上,看到了一个生命在时间面前经过了肉身与灵魂的被切割,生命再次完整的惊喜发生在了重新缝合在一起的刹那。即便在固态的时间的不断挤压下,它依然释放出让人惊异的光泽,那绝对不是残次品,在那个远古的时间里,人们因为它所释放出来的独有的美,而把它切割成两半,美被分成两半,一半美留在了这里,一半美带到了那里。我发现最终考古学家与我谈论的,其实已经是有关古瓷片的美学问题。他所在那些表面上往往是荒凉破败的废墟之上,看到的和追寻的不只是废墟本身,而是废墟之下的世界,让人惊讶的特立独行的美学暗藏在了那个世界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发现美的眼睛与挖掘美的能力与耐心。考古学家也知道,美的普遍性只能是一个悖论,并不一定在哪里都能发现美,人们一直所说的我们只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只是在一些时间里有着一定道理。
废墟:兵隳之地,至少经历了去兵隳般的破坏,眼前的世界寸草不生,在这样没有任何生命(至少我出现在那里的时候,没能发现任何的生命,连让人感到更加荒凉与惊悚的乌鸦都没有出现,其实乌鸦已经在很长时间里消失不见,在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把乌鸦和废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总想把它们放在一个空间里,才会觉得那个空间没有任何怪异的因子),这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废墟没错,至少是我所对废墟的认识就是这样的。与我一起出现在这里的就是那个考古学家,这时先让我们把废墟放在一边,先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废墟有着一定关系的考古学家,说白了如果没有考古学家对于那片废墟的期待,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考古学家是一个异常沉默的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沉默,他常常梦见自己是一个古代的瓷片,一个破损的瓷片,一个一直在寻找着生命完整的瓷片,他总觉得这样的梦类似神启,在那之前他是挖掘到了一块破损失去了另外一半的瓷片,在那之后他又找到了另外一半,但这只是他所做的梦之一,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梦,在这些梦前,所有人类的想象力都将无地自容,但他没有跟我讲起其他任何一个梦。考古学家用寥寥几句话跟我说起,自己在挖掘那些废墟时是小心翼翼的,但他的工具又特别锐利,他总觉得自己刺向那些生命的黑暗时,就需要一把锋利的刀,就需要一些锋利的工具,还需要一颗锋利的灵魂。考古学家常年在怪异的梦中醒来,他多次在黑夜中拿起那些工具,来到某些废墟进行挖掘,但是他在黑夜中不曾挖出任何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在黑夜的漆黑之中,他那双对于美有着敏锐感觉的眼睛,失去了它的敏锐。在这个废墟之上,他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事,我多少还是感到不可思议,眼前的他是一个怪异的人,眼前的他在对于时间和空间异常着迷之后便成了现在这样的人,一个在我面前只是有些沉默的正常人,但在那么一些夜里,他便变得不正常了。黑夜之中,一颗跳舞的灵魂,一个被神灵召唤着在夜间醒来的灵魂,那已经成为了他命运无法避开的一部分,他说自己认命了,本来在开始之初,他感觉到内心里面,每到夜间更为躁动对于古老的想象更为渴望到无法抑制的程度,他多少有些慌乱,也常常压制自己,但某天夜里他控制不住之后,当他来到了繁星之下的废墟之时,他拿出了考古的工具,当听到了夜间的废墟之上的虫鸣与自己的工具挖掘之时发出的声音交汇在一起,他便彻底释然了,他便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对于美的追寻者,即便到现在,他还从未在黑夜中挖掘出任何东西。我也希望自己能在某个黑夜,在繁星密布之时来到那里,想好好聆听一下美妙的虫鸣,毕竟我在白日里的现在出现之时,真没有任何虫鸣,真是一片荒凉之地,一个会让人感到绝望的荒凉之地。
那时我成了一个在很多人的世界之中的不适者,我可能也成了一个神经质者。远离那些喧嚣的漩涡(努力从中抽身),我出现在了那个山谷之中,山谷的景色很美,山上的草甸青葱美丽,水流汩汩流淌,流过那片草甸的根部,但在那个世界里生活的人很少,只有更多废墟式的建筑,似乎那时我要的不是废墟,而是眼前的草甸,以及草甸上流淌的河流,以及草甸上悠闲生活着的羊群。
废墟:废墟一样的古城,一座正准备被修复的古城,破败不堪的表象,以及同样疲惫不堪的内里。它早就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在人们制造那片废墟的过程中,只有很少的人感觉到痛心,更多人选择了沉默。语言与沉默。乔治·斯坦纳。批评家,或者是文艺批评家,或是文学批评家,或者是思想家,或者是文体家。如锋利的刀刃,如忧伤的苇草,如遥远的星辰。斯坦纳面对的是人文精神渐趋没落的现实,自我思想流放的现实,语言在极权主义面前的衰落,以及语言所受到的多个方面的挤压。面对重要作品时,灵魂的战栗与苏醒。伟大的写作与伟大的批评。“有些精神扎根于沉默”。感受力的重要:感受力的自由,感受力的萎缩与脆弱。对于时代的锋利切入,时代里所蔓延的欲望以及人性所面临的枷锁,以及独特个体的回声的消亡带来的悲痛,以及人类心灵最为积极的一面,以及最为消极的一面。自我感受力最终的毁灭。语言布满了瓦砾与刺鼻的碎片。在时间之墙上留下影子的大师们,他们难免被扭曲,他们难免要面对光荣与暗影的携手并行。面对着众多隐藏于内部的荒凉之声,语言的骨头被投入痛苦而荒诞的废墟。我开始想象着:现在人们又开始了修复,修复的过程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进入了那个正在准备被修复的古城。一些人之间争论得面红耳赤,大家都觉得应该修复它,却其实没有人能真正明白,该如何去结束那些一直萦绕不去的东西。在还未完全被修复以前,古城的概貌更多是残片的,残片的一种聚集。(作者:李达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