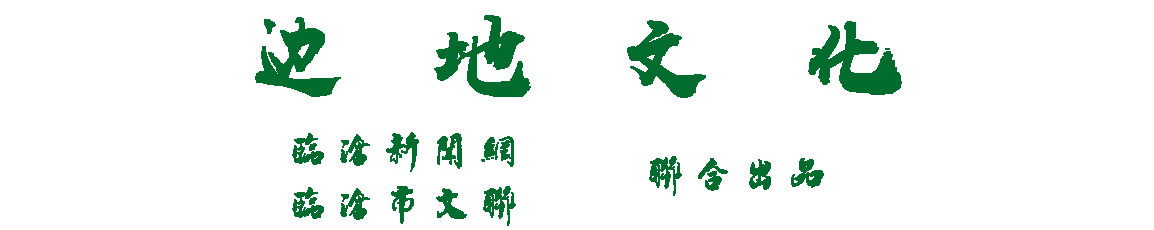
佤族是云南的特有民族和跨境民族,是新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由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个社会经济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佤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均依赖丰富的口传文学口耳相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佤族作家董秀英的出现,才终结了佤族文学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在各级作协的关怀和培养下,一批批佤族作家的迅速成长,佤族文学创作也在民族性书写的探寻和突围中崛起,有四位作家荣获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殊荣,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创作领域均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佤族文学也成为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
佤族书面文学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解放军挺进大西南的脚步,聚居于西南边疆阿佤山区的佤族进入了以军旅作家为代表的一批汉族作家的视野,创作出了一批反映佤族社会生活画卷的作品。但作品主要是从政治解放的视角,以“他者”的眼光和先进民族的审美立场去表现一个民族的新生和进步。佤族口传文学蕴涵着的天孕地育的恒久信仰和对生存神秘性的咀嚼与感恩,没能真正构成民族文学的表达和审美主题。直至1981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时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拉祜语主播和编辑的佤族作家董秀英,在军旅作家彭荆风等文学前辈的鼓励和悉心指导下,在《滇池》文学期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木鼓声声》,才终结了佤族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拉开了“以我手写我族”“以我手我写我心”的佤族书面文学的序幕。正如著名作家彭荆风指出的那样:“虽然第一次写作,文词、结构都较稚嫩,却写得朴实、清新、有感情。我很高兴,佤族这人数不少的民族,终于出现了第一篇文学作品,这可是‘创世纪’。”
在之后短短的10年间,在各种文学思潮流派此起彼伏、“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蓬勃兴起的语境中,在中国作协、云南省作协和文学前辈的扶持和提携下,董秀英携带着故乡佤山的文化因子和浓重的母族文化气息一路狂奔。相继创作发表了《洁白的花》《海拉回到阿佤山》《佤山风雨夜》《石磨上的桂花》《九颗牛头》《最后的微笑》《河里飘来的筒裙》等十余个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连续斩获了“云南省‘民族团结’征文一等奖”、“云南省1981-1982年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首届云南文学艺术创作奖一等奖”、“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等多项文学殊荣,成为了新时期第一批民族作家群中一颗闪亮的明星。1991年,董秀英以《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为名结集出版了佤族第一本书面文学集;1992年,董秀英的长篇小说《摄魂之地》横空问世。在短短11年的时间里,董秀英以自己的坚韧、勤奋、才情和文学担当,以佤族丰厚的民间文学为基石,从短篇、中篇到长篇,从散文到报告文学,以一己之力支撑和推动着佤族书面文学一路向着“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目标迈进。并在这样强大创作梦想的推动下,不断展开民族性书写的探寻与突围,以其“并不算圆熟的文字”传递着佤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大山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以其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文学审美在当代文学界引发起持久的震撼。
纵观董秀英的作品,不难看出以她为代表的第一代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经历的从“乡土批判”、“伤痕文学”到“文化寻根”,再到部落族群文化审美重建与回归的努力。在董秀英以《木鼓声声》《洁白的花》《佤山风雨夜》为代表的早期作品中,虽然因为与生俱来的佤族文化身份和佤族部落的成长背景,使得她得以以“在场者”的身份、以部落族人的审美立场,去展示佤族真实生动的历史过程和鲜为人知的民俗生活画卷。但却像大多初涉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样,在政治解放、“民族的新生和进步”为主题的“仿写”过程中,无声继承了新旧对比、对“落后”部族文化的批判和对解放赞颂的审美立场,使作品打上了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二元对立的时代烙印。以佤族猎头祭谷、剽牛祭祀习俗为代表的传统习俗,以及与之相应形成的礼俗文化,成为了被批判、需要被扬弃、革新的陋习。
然而,正是经历了这样的学习、模仿,董秀英创作日益成熟,沉睡于体内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在这样的民族性书写中日渐觉醒。正如彝族作家、评论家黄玲在指出的那样:“很多作家都是在民族文化的熏染下形成自己对世界的态度。一旦进入写作这一精神活动的空间,对母族文化的依恋和回望,会不自觉地贯穿于作品中。那是作家精神家园的根之所在,灵魂的归宿地。”带着“让你那古老、深沉、悠远的声音响彻阿佤群山”(董秀英《木鼓声声》)的雄心,董秀英决然放弃了“乡土批判”的审美立场和“伤痕文学”的干扰,开始调转写作视角,立足于母族文化的审美立场,带着自第一篇作品诞生之日起就暗含着的强大母族文化烙印,以其独特的民间文学叙事风格和母族文化深刻的体验,创作出了《背阴地》《最后的微笑》《九颗牛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等一批作品,自觉踏上了部落族群文化审美的探寻、重建与回归的历程。
短篇小说《九颗牛头》中,董秀英完全放弃了之前作品中对母族文化批判的立场,以母语部落族人的内部眼光和文化视角,讲述了佤族老人岩嘎为了实现父辈、自己“剽牛给寨子人吃、做一回真正的佤族男人”的夙愿,几乎用尽了一生的努力。当他一次性拿出九头牛来剽杀,成为了寨子中除头人岩松外剽牛最多的人家时,“看着墙角九颗齐展展的牛头,双眼紧紧地闭上了双眼”。没有对“落后”文化的批判,只有对母语部落族人价值取向和文化审美的深刻探寻和透视。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和长篇小说《摄魂之地》,虽然未能完全摆脱母族文化的批判和对女性苦难命运控诉的立场,但无论是对人物的塑造还是文学的叙事,均摆脱了初入文坛时的生涩和拘谨,以一种回归母族文化的开放姿态和文化自信,以带有母语鲜明特色语言韵律的叙事和部落族人内部的文化审美,展开了语言的“冒险”和民族性写作的突围,推动着表现主体与语言意象的和谐与完美融合,丰富了民族文学创作的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特殊的审美内涵。
佤族文学的崛起与繁荣
1996年,正当文学界为这位赤着脚从马桑部落一路走来、昂首走向世界的佤山之女欢呼之时,47岁的董秀英却因病英年早逝。当文学界发出“刚刚兴起的佤族作家文学,是否会因为她的离去而夭折?”的质疑时,1997年,由佤族诗人聂勒出任责任编辑、云南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个佤族作家文学集《花牛梦》正式出版发行。全书收录了埃嘎(肖则贡)、袁智中、王学兵、萨姆·荣哉·茹翁、李明富、陈辉、李宏英、赵汝美、吴芳兰等近年来活跃在佤山沧源10名佤族作者的11篇代表作。其中,李明富的《鸡头恨》不仅荣获得了本土期刊《佤山文化》1990年短篇小说征文一等奖,1991年还被《民族文学》全文转载;埃嘎(肖则贡)的《汉人》分别荣获了1991年《佤山文化》短篇小说征文二等奖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全省联合征文”优秀创作奖;短篇小说《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和《铁匠尼劳奥》则是袁智中、王学兵发表在《边疆文学》的处女作。这些佤族作家不仅与董秀英有着现实情感上的联系,在创作上也一直沿着董秀英开辟的民族性书写的道路跋涉。也正是在该文学合集出版的同年,袁智中的书信体短篇小说《最后一封情书》荣获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新人新作奖,成为了继佤族作家董秀英之后获此殊荣的佤族作家。
自1991年步入文坛的十余年间,在中国作协和省、市作协和文学前辈的培养和提携下,袁智中一路扬帆,先后创作发表了《女人心》《夫妻之间》《木鼓魂》《欲望的飞翔》《守护爱情》《丑女秀姑》《最后的魔巴》等十余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落地的谷种 开花的荞》,并于2006年结集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最后的魔巴》。之后,袁智中放弃小说创作,转向了以民族记忆重建为目的文化散文创作,先后在《民族文学》《边疆文学》《文艺报》等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失落的木鼓》《挂在崖壁上的文化》《石佛洞和石佛洞人》《牛的葬礼》《远古部落的访问》《小城的魅惑》《翁丁之旅》《走失的文明》等十余篇长篇文化散文,2007年结集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远古部落的访问》荣获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曾经出任第一部佤族短篇小说集《花牛梦》责任编辑的佤族编辑聂勒,也在新时期文学语境中,以诗歌创作的方式在民族文学界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自1994年开始汉语诗歌创作以来,聂勒先后在《诗刊》《民族文学》《青年文学》《边疆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近百首诗作,先后荣获了《青年文学》《民族文学》诗歌奖和《边疆文学》《云南日报》文学奖。2004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心灵牧歌》荣获了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不仅成为了佤族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版个人诗集的诗人,也成为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佤族诗人。2006年11月,聂勒作为唯一的佤族作家代表,参加了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同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我看见》。
在这样日益繁荣的民族文学语境中,在各级作协的关心和培养,又一批佤族作家悄然崛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作家伊蒙红木和诗人张伟锋。
2004年创作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以来,伊蒙红木就带着佤族魔巴之女特有的魔幻思维和语言质感一路高歌闯进文坛。先后在《民族文学》《芳草》《青年文学》《边疆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了短篇小说《阿妈的姻缘线》《母鸡啼叫》和《悠悠谷魂曲》《银象奔驰的地方》《沧源崖石上的精灵》《嘎多记忆》《我的老木鼓》《感恩母土》等多篇散文和诗作。2011年11月,伊蒙红木作为唯一的佤族作家代表,参加了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2012年,伊蒙红木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该书不仅为她赢得了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殊荣,还让她赢得了第八届湄公河文学奖。2016年伊蒙红木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云月故乡》,诗集集开天辟地、神话传说、民族迁徙、动物故事、童话歌谣、祭祀歌舞于一体,以佤族创世史诗和民间古歌的独特文化气息和语言叙事,为诗歌的民族性书写注入了一种清新的活力。
而与此同时,出生于1986年的佤族诗人张伟锋也异军突起,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边疆文学》《大家》《飞天》《山东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近百首诗作,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先后出版了《时光漂流》《风吹过原野》和《迁徙之辞》三部诗集,先后荣获“2014年滇西文学奖”“第六届高黎贡文学节提名作家”,成为云南诗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佤族书面文学不仅后继有人,且呈现出一种繁荣的景象。
民族性书写的探索与突围
正如董秀英自步入文坛之日起便责无旁贷肩负起民族文化的代言和民族文化记忆书写的责任一样。成长于新时期文学语境的佤族作家们,在经历了短暂的“仿写”“精神流浪”之后,便沿着董秀英所开辟的佤族文学之路,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形式展开了民族性书写的探索与突围。
自1991年,在《边疆文学》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后,袁智中便带着佤族族裔的鲜明标识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在经历了数年以女性生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创作之后,2001年袁智中发表了短篇小说《丑女秀姑》(《边疆文学》2001年第2期)。这篇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和审美特点的作品问世,成为了袁智中自觉性的民族性书写的一个重要拐点。2002年11月,在相距不到一年的时间,袁智中在《边疆文学》发表了自己的首个中篇小说《落地的谷种 开花的荞》。在这篇带有鲜明家族记忆的小说里,袁智中用带有母语鲜明特色的语言韵律,以一名部落成员的身份和审美视角,以佤族部落头人达丁女儿叶隆姆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展现了佤族部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以及与汉民族交往融合的发展过程。在小说的叙事中,作者抛弃了传统写作惯用的政治话语和叙述视角,采取人文表现视角和民间话语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佤族姑娘叶隆姆与部落猎王艾社·亚茹翁和汉人吴之间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充满民间叙事的魔幻手法的穿插运用,为作品注入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审美意味。评论家黄玲认为:“如果说这个中篇小说是袁智中题材转变的尝试,那么应该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体现了多年来她对佤族文化的思考与感悟,也是她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心理回归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是继董秀英之后又一篇表现佤族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力作。”(《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袁智中也凭着这一篇力作,斩获了“2002年度《边疆文学》奖”。自此之后,袁智中在民族性书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以2007年出版的佤族文化散文集《远古部落的访问》为标志,以非虚构作品的方式,肩负起了在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中,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民族、为本民族文化的保持与保存寻求突围的民族性书写的重任。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中,以“在场者”的身份,以血浓于水的深情去观察、记录佤族的历史文化和生存现实,让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化记忆重新变得鲜活起来,成为了佤族作家的共同选择和文化担当。
自200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伊蒙红木的作品便以她作为佤族魔巴之女特有的魔幻思维、语言质感和从佤族民间文学汲取的丰厚营养,引发了文坛的关注。她的作品中时常充斥着这样的富有魔幻色彩的语言:“召望(魔巴)的剪刀在半空犹豫了片刻,然后从中间迅猛剪断连接阿妈阿爸象征姻缘的棉线。两段棉线从阿妈阿爸手中没落,像失魂的飞鸟。”“从今往后,青藤不再缠大树,妇人,你生不是刘家人,死不是刘家鬼,刘家格龙神与你毫无瓜葛。”(短篇小说《阿妈的姻缘线》)在这样充斥着浓厚民间叙事的韵味中,总是让人隔着时空寻觅到还未曾远去的董秀英文学叙事的踪迹。
2004年,涉入文坛不久的伊蒙红木背起行装,以返回部落的写作姿态踏上了母语部落族群文化的重建之旅。并用长达六年的时间潜心创作了30万字的报告文学《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再现佤族渐行渐远的远古部落、远古习俗、现存文化现象、生存境遇、生活现状、精神状态和文化风貌。因为与生俱来的佤族文化身份和佤族部落的成长背景,使得伊蒙红木在展示佤族真实生动的历史过程和鲜为人知的民俗生活画卷时,不是站在异族文化的审美立场,或者是以一个观察者、窥视者的身份去展开的一种调查和文化解读;而是以“在场者”的身份和“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光”,站在部落族人的审美立场,去回望佤民族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讲述佤族远古的传说、村落的故事和佤山的传奇。在讲述佤族猎人头祭谷、剽牛血祀、部落纷争、等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以及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祭祀文化、文化礼仪、风土习俗时,不是站在文化革命、道德审判、二元对立的审美立场,而是站在本民族文化发展的特定历史长河,以第一手丰富详实的田野调查资料切入,以一名部落族人的文化自觉,进行生动的讲述和忠实记录,不仅让全书打下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烙印,也为自己的民族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
2010年,另一位佤族作家布饶依露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神树的约定》,用3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了自己数十年间“走出民族”和“返回民族”的心路历程。
正当袁智中、伊蒙红木、布饶依露等佤族作家们沿着董秀英开辟的文学之路一路前行时,佤族诗人聂勒带着阿佤的阳光气息,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坛上激起一阵回响。“用不着太阳/介绍 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条小河的主人/用不着绿叶/解释 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座山寨的美梦/……真的不用告诉你/我是一个古老部落/落难降生后的幸福”聂勒这位佤族的歌者,就这样带着阿佤山的炽热和天真,在一路高歌中开启了佤族诗歌创作的先河:“一千头牛的婚礼/在一个小山村里举行/新郎是太阳 新娘是月亮/主婚人是我们可敬的梅吉//一千头牛的婚礼/在一个小山村里举行/新郎是艾不拉 新娘是叶门嘎/牵线是我们聪明的达太//一千头牛的婚礼/在一个小山村里举行/一千头牛彩礼靠勤劳获得/美丽的姑娘不嫁懒汉……”(《一千头牛的婚礼》)。正如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为他的诗集《我看见》作序写道的那样:“作为一个民族诗人,他们所进行的诗的创造,都为他们各自的民族树立起一座精神的高山。”“我一直对一种诗人怀着深深的敬意,那就是他们能把自己民族的原生文化与独特的诗歌美学观很好地融合起来,同时其作品又具备了强烈的现代意识。”“我为这个世界上有洛尔加而感到幸福,同样我为佤族有一个像聂勒这样的诗人而感到欣慰,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诗歌,捍卫了人的权利,并为这个世界的光明和未来歌唱。”
2010年代,云南诗坛迎来了另一位80后佤族诗人张伟锋。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这位80后佤族后裔不仅接连出版三部诗集,诗作也连续被《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边疆文学》《大家》《飞天》《山东文学》等十余家文学期刊采用,成为了继聂勒之后文坛上最为闪亮的佤族诗人,其中诗集《迁徙之辞》被列为2015年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重点作品项目扶持推出的作品之一。
在新世纪文学场域中,当大多数80后、90后诗人将诗歌书写指向城市生活的时候,拥有佤山成长背景和完整现代汉语教育双重背景的张伟锋,却将书写的视角指向乡村和母语部落,让他的诗歌打上地域文化和母族文化烙印的同时,也让他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获得一种全新的视域和表达:“……今年的雨水特别少,今年的谷子不抽穗/今年的穗子不饱满,今年的寨子遇火烧/今年的饥荒来到了佤山,今年的苦难降临佤寨/……神啊,我们挥动了刀斧/砍下最茁壮的树木,拉运回来敬献给您——/神啊,请别让我们的灵魂摇曳不定/请别让我们的言辞和行为触犯您,请让我们的粮食堆满仓库/让我们的族人兴旺发达,站满山冈——”(《拉木鼓》)虽然这样的表达有时候会带着些许淡淡的忧伤:“他们不知道异乡。他们的忧愁都是假的/刨根十年/我才看清流浪的面貌。我必须返回旧地/告诉父亲和母亲/我们有故乡。方向在何方,地点在何处/有朝一日总会知晓。外公已经去世/外婆跟随西游。他们必须在隔开的世界/同我拾起这个迁徙之辞/拾起那些丧失的苦痛和寒冷/返回故乡”(《迁徙之辞》)但却让张伟锋在这样超越地域和身份局限中为诗歌的表达注入了张力。
伊蒙红木的诗集《云月的故乡》则以其特有的佤族民间诗歌的语言韵律,拓展了佤族诗歌表达的边界,为母语部落族群文化审美的探索、发现、重建与回归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此期间,王学兵则放弃了创作颇丰的小说、诗歌创作,毅然决然返回民间,历经十数年的收集整理,于2004年出版了散文体佤族创世纪神话《司岗里传说》。
民族性书写的困境与挑战
以1981年董秀英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木鼓声声》为标志,佤族书面文学已走过了三十八年的发展历程。三十八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各级作协组织的关心、扶持和培养下,佤族文学创作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创作领域均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纵观佤族文学的三十八年发展历程,也不能不看到,在新时代文学语境中,佤族作家民族性写作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小说创作上。继董秀英之后,以袁智中、伊蒙红木、王学兵、肖则贡、李明富等为代表的一批佤族作家先后在《民族文学》《边疆文学》《青年文学》等文学期刊上发表了20余个短篇和中篇小说,结集出版了《最后的魔巴》《花牛梦》《神林山寨》等中短篇小说集。但无论是从作品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还相当薄弱,无论是短篇小说创作还是中篇小说均未抵达董秀英创造的高度;在董秀英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摄魂之地》创作发表长达27年的时间,仍然没有一部佤族长篇小说诞生的纪录。
与小说创作相比,散文创作看似取得了重大突破和丰硕的成果。佤族作家们不仅先后在《民族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边疆文学》等多家文学期刊上发表散文作品,袁智中、伊蒙红木、布饶依露还分别出版了个人的散文集。其中,袁智中的散文集《远古部落的访问》和伊蒙红木的散文集《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分别获得了第九届和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然而,文学指向的“民族性”写书,除了对这个民族千姿百态的社会风俗画和人文风景线的描绘外,更重要的是对这个民族情感最生动丰富的表达和对其精神最深刻的诠释和记录。在对新时期佤族文学创作的回望和审视中,便会发现,继董秀英之后,在新时代语境中,佤族作家在成功逃离“乡土批判”、“伤痕文学”的影响和束缚,以返回部落的写作姿态开始了文化的“寻根”与“扎根”之旅时,却再度跌入了狭隘的“民族性”书写的泥潭。佤族作家在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大量书写和记录中,忽视了在一个城镇化迅速启动国度下,在民族文化出现历史断裂的深谷中,对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尖锐的书写。在“返回民族”和“走出民族”的艰难探寻中,由于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尖锐、深刻的观察和思考,使“民族性”书写长期停留在对传统礼俗文化和风情民俗的刻意展示和表层记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在边缘部族文明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时代,缺席了文学对自己民族过去与当下处境的记录和书写,在重塑民族历史记忆与际遇中显得苍白乏力。
所幸的是,以布饶依露、袁智中、聂勒、伊蒙红木、张伟锋为代表的佤族作家们,仍然在董秀英所开辟的佤族文学的创作之路上坚持不懈地实践着、探索着。(袁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