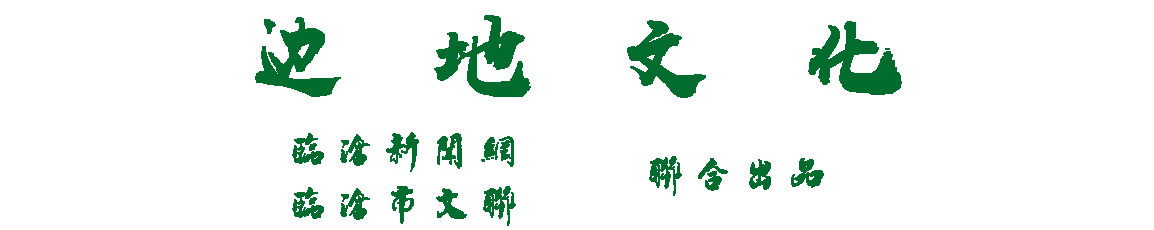
佤山日记
/邵智颖
诗和远方?
我承认当我第一次看佤十班学生跳舞的时候,我被感动了,他们赤脚把地板跺得很响,跳起舞来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发出“西赛赛”的声音,跳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甚至想流泪。但是不管舞蹈再怎么好看,依然阻止不了我想要离开这里的心。
我被困住了,大学刚刚毕业就被困住了,困在这弹丸之地,没有可以好好逛街的地方,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最主要是没有老吴。我开始在心里一遍遍暗骂那个把我招来的校长,他骗了我,他告诉我,我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搞创作,不用上课,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可是实际上呢?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自己就像坐牢一样,每天上班下班打卡签字,做着太多太多无意义的事情,我无时不刻不在盘算着怎样离开这里,这让我想起电影《天浴》,满腔热血的下乡当知青,最后发现乡下不是诗和远方,而是无处不见的荒芜和走不出的大山。可是我如果违约了,必须要赔两万块违约金,我刚刚大学毕业,去哪里找两万?跟父母要?我开不了口。选择是自己做的,那就待到攒够两万块,把违约金交了走人。我甚至想过,如果我主动辞职算违约,那么如果我被开除的话,应该不算我违约吧?可想而知,我是报着一个想要被开除的态度在当“老师”。我应该是全世界最不像老师的“老师”吧,我在想。
上班经常不打卡,早退,学校安排的任何除了教学以外的杂事从来不做,年轻的心总是天不怕地不怕,校长找我谈话无数次,软硬不吃,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也没辙了。害怕晒黑变丑,老吴退伍回来不认识我,所以出门总是戴着口罩,打着伞。周围的人应该都觉得这里来了一个怪胎,天气好好的又没有下雨,干嘛整天打伞。好吧,我说实话,因为我觉得佤族人比较黑,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基因问题,也可能是因为沧源紫外线太强,所以别人问起我为什么要打伞,我懒得解释太多,总是谎称“紫外线过敏”。每当太阳落山,看着夕阳西下,我就开始想家,尤其是我对面的同事弹吉他唱起佤歌《想你》我的眼泪就流个不停。老吴新兵入伍,所以不能随时给我打电话,每个星期只可以有几分钟的通话时间,那个时候我就把我们的通话录音,每天晚上听着我们打电话的录音睡觉,他说,“我数过了,我这里的天空每天飞过三架飞机,当我数到第2190架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我了”。隔壁缅甸打战的时候,有炸弹不小心飞到了隔壁县,有农民家的牛被炸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经常会想,会不会有一天运气不太好,炸弹就飞到我跟前,我还等不到2190架飞机飞完,就“嗝屁”了。天呐,好危险,我还是赶紧攒够两万块,卷铺盖走人。
与十班的交锋
对于十班的学生,刚开始当班主任的时候我是不情愿的,这个班主任当的算是赶鸭子上架。别的班主任吧,都像保姆,我这个班主任当的吧,还挺轻松。心里没有责任,当然轻松!学生对我吧,其实也不太喜欢,我总结了:一,他们的生活我不管不顾,但是接触到舞蹈专业课的时候,我却凶得像母夜叉。二,他们说我不了解佤族,不了解他们的性格,跟我无法沟通。三,每次我们有冲突,他们就会私下用我听不懂的佤话“叽里呱啦”,不用猜也知道,肯定除了骂我以外,没有一句好话。四,他们会委屈的去跟校领导诉苦或者可以称之为告状,说想换班主任。我心想,你们不喜欢我当你们班主任,我还不稀罕呢!
我和十班的矛盾最终还是爆发于我接他们班主任几天以后,那天我刚刚走进舞蹈教室,学生的脚气就快把我熏得晕过去,他们是习惯上课不穿鞋子的,每次下课前我都得反复提醒下次来上课前记得洗脚,这不,又没洗脚,再加上我昨天刚教的舞蹈组合,第二天就全部忘记,那时的我很生气,一气之下罚全班同学“劈叉”半小时,可才刚刚十分钟,就有男生站起来摔门而去,紧接着,其他同学也纷纷跟上,跑出教室,他们看我时候那眼神啊,全是敌意,我都怀疑他们晚上会不会乘我睡着,把我反锁在宿舍,再给宿舍点上一把火!那时的我也像是一个叛逆的22岁的大孩子,而他们是一群叛逆的小孩子,全部撞一块儿去,那就是原子弹爆炸。我不觉得我是老师,只觉得你们不让我舒坦,我也不让你们舒坦,反正大不了这个班主任我不当了,这个老师我也不干了,两万块另谋他处!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想当初,满怀热切的来这里搞创作,到头来还得受你们这群小娃的气?没有的事儿!
我和十班的僵局持续了很久,我觉得我们都是“狗不理”,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上完课走人,多一分钟都不想在他们中间待,直到那天中午,十班语文课老师字老师给我打电话:“邵老师,你们班学生上哪儿去了?我来教室不见人呐”。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知道”。字老师:“不知道?你是他们的娘,自己的儿去哪里了都不知道?”。她这句话让我久久缓不过神来,“我是娘?娘?哦·····娘”。
“敌我关系”的缓和
那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饭,食堂一般只有两个菜,一荤一素,米饭硬得像子弹,完全无法下咽。打好饭正准备坐下吃,四下一看,我们班最调皮,就是那个带头走出教室的男生卫华,他的碗里只有饭没有菜,旁边的老师说,他家庭困难,为了省钱,每次只吃饭。我走过去,抬起他的碗,“走,老师请你吃菜!”他说“不用!”,并一把抢过碗,跑了。我如今想起来,当时的举动是不是伤害到他那年轻的自尊心了?周末的时候,我去农贸市场割了几斤肉,买了葱、姜、蒜、小米辣,按照食堂大妈教我的方法,炒了肉,舂了他们最爱吃的“抓”。小米辣飞进眼睛里,辣得鼻涕眼泪流一脸,我把炒好的菜分几个袋子装好,每个宿舍分一点。学生说很好吃,第一次我做的菜竟然受到了夸奖,他们开心,我也开心。从那以后,我每个周末就早早的去农贸市场买新鲜的菜,做好,带到学校里面去。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菜一袋又一袋,慢慢的,他们看我的眼神柔和了下来。
经常有老师跟我反映,“你们班那几个男生太让人头疼了,一会儿上课睡觉,一会儿迟到,你看,今天又旷课了”。我把调皮的那两个家伙找来。我先问卫华“你为什么上课老是捣乱?” “我坐不住,我都打算拿了这个月的助学金就不读书了。” “那你喜欢干什么?”我接着问 “也没有什么喜欢干的,回家就种地。”“你喜欢种地么?”他想了想回答“种地比读书容易。”我接着问肖光“你呢?天天旷课也是因为坐不住?”“我在家摘茶,帮我爸妈赚钱。其实我也不想读书了,回家还可以帮家里赚点钱。”“你喜欢赚钱么?”“我的理想就是以后当老板。”“好的,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次日,我在学校里面找了一块空地,并隆重宣布任命卫华为我们班的“国土资源局局长”,并安排给他一个小分队,我买来了各种各样的菜种,告诉他“我们班以后的伙食就靠你了”。从此以后每个周末回家,我们班同学都被“国土资源局局长”安排了任务——每个人捡两斤牛粪拿来学校。有的同学把牛粪忘记在家了,急的赶紧打电话给他爸,他爸骑着摩托拉来一大口袋牛粪,当全班同学看到那一大口袋牛粪的时候,感觉眼睛里的光芒都要蹦出来了,把牛粪扛下摩托车的家长仿佛身上都散发着金光。另外,我还任命了肖光为“外贸交易部部长”,他主要的任务就是,等卫华小分队把菜种出来了,组织同学们把菜拿到农贸市场去卖,虽然我们的菜一直种到他们毕业都还不够内部消耗,但是远大的理想还是要有的,说不准有天就实现了。除此之外,他还要负责组织一个小分队,到学校收集废旧瓶子、书籍、报纸,到周末,我们跟学校借着三轮车,拉到废品收购处,这样一来,我们就有钱了!那个时候,我们班教室的角落,不是堆着废品,就是牛粪,没有少被其他老师投诉。但是感觉每个孩子的每天都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每天来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们班的小菜地,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了,但是,至今我想起这个画面依然动容——一个从来没有种过地的女老师带着一群小黑娃,每天蹲在散发着牛屎味的菜地里,观察菜今天比昨天长了多少,估算着,还有几天菜芽会出土,还有几天才能吃,还有几天才能卖。牛屎味、土味、笑声、还有那时的阳光。好像待在佤山没有那么痛苦了。慢慢的,我们班这两个调皮的家伙,变乖了,也不说要辍学了,我们都自得其乐。
当然中间也会时不时的有学生跑来“老师,我不想读书了”。“为什么?”“因为校长说我头发太长了,叫我去剪”“那你就去剪啊!”“可是我没钱”,好吧,我从兜里掏出五块钱递出去。次日,“老师,我又不想读书了。”“为什么?”“校长说我头发太黄了,叫我去染”“停!我知道你没有钱。”好吧,只能去买来染发膏,挨个给他们染头发。
日子这样不紧不慢的过着,我还是每天等电话,等老吴一个星期才可以打一次的电话,我告诉他我想去昆明看他,他说:“你别来,我好不容易适应了部队的生活,一看见你,又不知道要多久才能重新适应。”所以在他当兵这两年里,我没有去看过他一次。
“十班”和“依怜”和“叶斯嗒”
我认识一个佤族小伙子,在沧源卖啤酒,他在仓库里捡到一只小奶猫,他对我说:“这只小猫好可怜,它的妈妈把它的兄弟姐妹都吃了,我发现它的时候正打算吃它,还好被我救下来,你想不想养?”。我想着在沧源那么无聊,家里有个活物每天等着我下班也是好的,就答应当它的养母。小伙子骑着摩托来给我送猫,他小心翼翼的从衣兜里把小猫掏出来,叮嘱我要照顾好它。它那么小,还不会吃饭,我去超市买了最好的奶粉来喂养它。心想“小家伙,你的伙食比我还好了”。学生听说我收养了一只小猫,都想见见它,那天我把我衣服上的蝴蝶结拆下来,给它做了个小领结,带着它去见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见它,都抢着抱,班长让同学们排好队,每人抱一分钟。学生问我,“老师,它有名字么?”。我说:“没有,我们给它起一个吧!”学生就找来两张纸,一张上写着“依怜”一张写着“依唯”,我在前面唤它,它往哪张纸上走,最后它的名字就叫什么。它自己“选择”了“依怜”,学生说因为它被妈妈抛弃了,所以叫“依怜”也是最合适的。从那天起,我有佤十班这群孩子,佤十班又有了“依怜”这个孩子,准确的说,它变成了我的“孙女”,我的身份一下子从“养母”变成了“奶奶”。后来,在学校经常会看见佤十班的学生去食堂打饭肩膀上站着一只小猫,今天站在高个子肩上,明天站在小胖子肩上,大家都主动承担起照顾它的义务,在教室上课,角落里也会有它的身影。有时候学生生病了,来不了学校,会打电话问我“老师,今天依怜吃了些什么?它有没有用爪子挠人?”同学们觉得连我们的小奶猫都有佤名。那么我也应该有一个佤族名字,这样才显得我们是一伙的。他们给我起了一个佤名叫“邵叶斯嗒”,意思是绿叶上的露珠,他们经常会没大没小的称呼我为“叶”。我也会经常给同学们起绰号,比如,卫华他的头长得像一个可爱的小南瓜,我给他起的绰号就叫阿瓜。没有绰号的同学,就称呼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小美、小月、阿光............。如今想起这些名字,他们的脸庞就一个个从我眼前划过,心里五味杂陈。
平静的日子被学校下达的紧急任务打破,要在一个月以内做出一个原创作品到省里参加比赛,时间紧任务重,从音乐制作到服装设计,全部要从零开始。我问同学们。“你们去过沧源以外的地方吗?”他们摇头。我问“你们想去吗?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吗?”他们点头,眼睛里面散发着渴望的光芒。我告诉他们,“如果走出沧源,你们代表的就不仅仅是自己,在整个中国,除了西盟以外,佤族最多的地方就是沧源。在外面的人看来,你们代表的就是中国佤族。我们要用这一个月的时间。让外面的人知道,佤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能给佤族丢脸!同学们,责任到你们肩上,必须扛起来!”同学们被我说得责任感爆棚,都满怀期待着要给佤族争光。
就在这紧要关头,啊瓜又旷课了,且连续一个星期找不到人。打电话到他家里,电话停机,我很着急。肖光告诉我。他们私下里有过联系。他家里面出了一些状况。啊瓜的爸爸前不久去逝了。这几天他妈妈又丢下了他和五岁的弟弟到隔壁村跟其他人过日子去了。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和五岁的弟弟,他不想读书了,想出去打工挣钱供他弟弟上学,帮爷爷减轻负担,我听来心里一阵酸楚,想着必须把他找回来。我当天就包了一辆面包车,托师傅把我拉到他们寨子。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带着弟弟在地里砍甘蔗,看见我的那一刻,还没有开口,我们彼此的眼眶都红了。我强忍着情绪问他“你不想去省里面参加比赛了吗?你不想去看看这个世界了吗?你就这样放弃了吗?”他低着头,压抑的哭着。我走过去,拉起他的手,坐上面包车,一路无言,彼此的情绪翻江倒海。我们到学校周边的小馆子。我点了他爱吃的菜,让他快吃。吃饱饭了以后我告诉他“以后我不会再把你当孩子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大人了,要争气,好好读书。要不然你弟弟和爷爷就真的没有指望了。”他点头,我把他送回了学校。
啊瓜安心的在学校待下,学校有免费的营养早餐,国家每年对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都有定向的补助金额,加上他家是建档立卡户,又能每个学期领到另一笔额外的补助,在学校的日常生活都不用太担心了,他唯有牵挂着他那年幼的弟弟,和行动不便的爷爷,在这里,不得不感叹国家的强大,能让这些孩子们安心的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我每个周都会轮换着把家庭困难的学生带到我住的公租房给他们改善伙食,我告诉他们:“老师做饭实在是太难吃了,我需要你们去给我弄两顿好吃的,你们看,我现在已经这么瘦了,如果再吃不到好吃的,我要瘦得被大风刮走了。”他们很能干,总是三两下就弄出不少菜,不过都是辣的,或者凉拌,我的胃不太好,吃太辣的东西容易烧的慌,学生说:“老师,您怎么不吃啊?我做的不好吃么?”勉强吃下,辣得我直流眼泪,晚上胃烧得睡不着,半夜起床找胃药。
我和十班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像师生,于我,他们更像是家人。班里的女生失恋了,会跟我说心事。每次去查夜的时候,男生宿舍都会有一个人放哨,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里面干坏事。放哨的会对着宿舍里面大吼一句佤话,我找佤族同事翻译给我他们佤话说的是什么,佤族同事告诉我,他们在说“妈妈来了,快点把东西藏好!”。我晚上熬夜追剧,第二天忘记去上课,在宿舍睡着了,当有督查室的老师去查课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会非常默契的帮我打掩护“我们老师已经来了,她上厕所去了”然后就会有同学跑到我宿舍楼下,用小石头砸我的门,压低声音喊“老师!老师!快起床,有老师来查课了!”。他们周末回家了,会给我带他们去山里找的各种野果。他们也开始习惯我母夜叉式的专业课教学,每次他们干坏事,让他们写检讨,他们检讨的最后一句话都是“老师,我会改的,我们爱你!”看检讨都感觉在看花式表白,又想气又想笑。啊瓜和一众男同学,还是会忍不住干坏事,比如上文化课睡觉,抽烟被逮到,半夜翻学校围墙等等。值周老师跟我说:“你知道昨天晚上逮到你们班男生翻墙,他们对我说什么吗?”。我疑惑的看着他“他们竟然说,老师你怎么罚我们都可以,就是求你不要告诉我们邵老师。”我说:“那我就当不知道吧!”。值周老师惊讶的看着我:“你不去骂他们么?”我笑笑,不言语。在其他老师眼里,我是一个多么不负责任的班主任,但是我想的是,他们怕我知道他们干坏事,该是觉得对不起我,所以他们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教育的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么?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的不好放大呢,他们只不过是想在我眼里倒影出他们美好的样子吧!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件无厘头的事,有一次一个男生来找我请假,说他爸爸病了,要回家,我批了。结果半小时以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哈哈,我们邵老师真好骗!”然后配上一张自己愉快玩耍的图片,他可能是太兴奋以至于忘记屏蔽我,于是我默默的在这条朋友圈下面点了个赞,是的,点了个赞,表示“好的,我知道了”。结果他二十分钟以后就回来了,我没有找他谈话,更没有骂他,结果他好几个星期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噩梦的开始
我想我的作品必须在内容上依附于传统文化,又必须在形式上脱离传统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创新。然而我忘记了,新东西出来,是不会被人马上接受的。
我们找农民做了一个直径有十米的大竹圈,我说:“岩散,我们必须干票大的,我们要拿这个大竹圈做个独一无二的项圈出来”。学校老师看见我们拿那么大的竹圈在教室里滚来滚去,都觉得我太儿戏,去找校长反映:“小邵太年轻了,还不能那么快就挑大梁,还是换别人来排吧,他们照这样下去,只怕是会丢我们学校的脸呐。”校长找我谈话:“小邵,你看你这个创作思路能不能变一变?”当然,谈话的结局我是不会妥协的。作品思路大概理清了以后,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出现了,就是我们的演员个子参差不齐,高矮胖瘦都有,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和岩散(我创作中的合作伙伴)商量好,第二天要去删减人数的,可是走进教室,看见佤十班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我迟疑了,我竟然下不去手。我当时做了一个非常不专业的决定,就是不删人,让我们全班都上,管他结局如何,我不可能辜负我的孩子们啊,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啊,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啊,我是娘,他们是儿啊!
平静的日子,似是在等待暴风雨的来临。因为我创作上的固执和任性,让人看起来太不靠谱,比赛任务也被学校安排给其他人,而我精心培育的十班也被其他老师接替了,我被安排去上汽修班,导游班的业余课。这时候,有多少次我想收拾行李走人了,可是放不下十班的学生,我上完课,十班的孩子们跑过来把我围住,“老师,我们好想你,为什么你不上我们的课了?你不在,我们没有心思上课,我们不要其他老师来上我们班的课”。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敷衍着说:“不管是谁上课,你们都要好好学习!”。回到宿舍我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黑暗的屋子里,倒头就睡,仿佛拉上被子就能隔绝我所有的烦心事。而我的小依怜也不知道吃错什么东西,睡了一觉醒过来,它已经僵硬的躺在它的小窝里,我抱着它小小的尸体,感觉全世界的绝望都在向我袭来,我给老吴打电话哭得声嘶力竭,我觉得我上辈子肯定是个水桶,水桶里装的都是眼泪。
人终究还是要站起来面对风雨,在请了几天病假以后,我调整好心态,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十班的同学们见我来学校了,开心又失望的说:“老师您生病了吗?我们本来约好今天放学去你家看你,你怎么就来了,你再请半天假回去休息,我们去看了你,你再回来上班。”看吧,冬天再冷我也不觉得冷了,我有那么多小棉袄,我怎么能懦弱?这群小棉袄最夸张的还是他们集体去威胁其他班上我课不老实的男生“我们警告你们,上我们班主任的课最好老实点,我们还在学校呢!”。这群在我眼里人畜无害的小绵羊,竟然为了保护我露出他们的獠牙和利爪。
事实上十班为我做的不仅如此,最后他们竟然全班一起威胁学校,如果我不回去教他们,他们就全部退学。校长怕了他们了,最后终于把他们还给了我,排练任务终于又回来了。我不忍告诉他们小依怜走了,他们问起的时候,我就说它被我送回老家了。
我们一起去“炸街”
紧张的排练接近尾声,我和艾散几经波折创作的舞蹈作品终于完成了!马上就要出发前,学生跑过来问我:“老师,我们那么黑,外面的人会不会笑话我们?”。我反过来问他:“我那么白,来到这里,你们笑话我了吗?”学生摇头。我说:“那就对了啊,我在这里,你们没有笑话我,你们出去,别人又怎么会笑话你们呢?如果别人问起你们,你们就把头抬得高高的,告诉他们,我们是佤族,我们民族的传统就是越黑越好看。我们是亚洲的黑珍珠,东方的野玫瑰!”我们穿上漂亮的佤族服装,戴上项圈,挎上民族包包出发了,我们在车上,一路的唱着歌,车子好像在带我们驶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舞台,那么多的观众,那么一流的灯光设备,我以为他们会腿软,但是我错了,他们真的是一群“人来疯”!。正式演出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第一次,我第一次在观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我居然自己把自己感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流泪到无法自制。他们在舞台上卖力的跳,我在台下卖力的哭,那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比赛结束,我们获得了云南省中职学校二等奖的成绩,我跑到下场口去接我的小英雄们,他们也好激动,七嘴八舌的说“老师,他们对着我们喊男神!”“老师我们好受欢迎啊!”。你能想象么,就演播厅到学生住处两百米的距离,他们走了两个小时没有走回去,一路不停的有人跟他们合影拍照,学生说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明星。第二天他们不再问我别人会不会笑他们皮肤黑这个话题,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老师,我们憋不住了。”我以为他们要上厕所,结果他们告诉我,他们想唱歌想唱的憋不住了!我说:“那就唱!”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一群身着民族服装的怪咖,在繁华的都市街道开心的,大声的唱着佤歌,不管旁人的侧目,快意人生,本该如此,我们“诗酒乘年华”!
比赛结束以后,孩子们更自信了,更加以自己的文化自豪了,并由衷的觉得自己黑的很美,我甚是欣慰。我也在“教师”这个职业里找到自己的价值,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像家人。时光如流水,我们的菜已经种第二茬,这群孩子的个子也突然往上蹿。他们成长着,我也成长着。
转眼,他们在校两年的时间已经满,按学校规定,他们第三年要到校外实习,我送他们走的时候,全班同学拥抱我,他们哭着说“老师,你要在学校等着我们回来,我们怕实习回来就找不到你了。”我忍着眼泪点头。两万块钱其实早已经攒够,可是我却留了下来。折腾了一大圈以后,突然发现,孩子们清澈的眼睛就是我爱的星辰大海,有他们的地方,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孩子们走后,我看着空空的菜地,空空的教室,我的心也空空的,就在我转头的刹那,老吴在教室门口朝我微笑,那个一直活在我口中的人,我的爱人,他退伍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