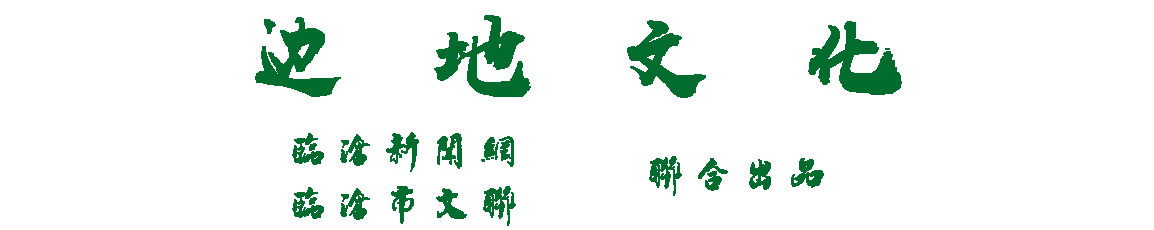
家 乡 的 冬 天
又到了冬天,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植物会凋零,动物会冬眠,候鸟会飞到较为温暖的地方过冬,也意味着沉寂和清冷,给人万籁颓寂的感觉。在人们普遍的印象里,冬天都是这样一副颓唐和萧条的模样,而在我的家乡却是别样的一番光景,因为每到春节前后黄锃锃的油菜花开满漫山遍野,染亮了整个小坝子,放眼望去纯粹干净,微风拂来时,花海摇曳生姿,美得轻盈剔透,让人沉醉其中。
我的家乡是一个秀丽的小镇——勐佑镇,勐佑一词来自傣语音译汉字的地名,是绿色小坝子的意思。勐佑坝子四面环山,顺甸河横穿而过,正好把坝子一分为二,因此河的东西岸就叫做河东和河西。我的家在东岸的河东村,依山傍水,全村人依缓坡而聚居,房子都是坐东朝西,所以河东的人们都说他们家的太阳是从房子背后升起的,而河西正好相反,因此他们又说太阳是从他们家的门前升起来的,一天之内河西人都比河东人要早晒到太阳,太阳也比河东人要早被房子遮蔽。
在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谚语时,我很气不过,我觉得世界上只有河东村才是最好的,而且河东会一直一直好,怎么都不会输给河西的……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天真单纯,也因为太小没有见过世面,判断事物从来都是根据自己的性情,或者通过大人的解释来的,想来确实好笑。
近些年来,我因为工作长期居住在外,每年回家的次数变得屈指可数,如今最令我感怀的还是家乡的冬天。冬天里勐佑人茶余饭后最喜欢围在火盆边烤火,因为冷得实在不想动弹,每家每户都少不了一盆暖暖的碳火,木炭也就成为了勐佑人过冬必备的物品。用一个简易的小铁盆,盆底放一层平时烧木柴余下的灰,我们叫灶灰,堆上几只木炭,就成了一个暖烘烘的火炉了。在别的地方冬天家里来了客人,都是一杯热茶招待为敬,而在勐佑则首先请客人到火炉边上烤火才为敬,其次才是上茶水。
上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冬天我第一次“出远门”,母亲带着我进县城姑妈家做客,60多公里的路程坐中巴车要两个半小时才到。那时还没有柏油路,都是巴掌大的石头铺成的弹石路,一路上车轮和路面的摩擦声,汽车的发动机声,嗑噔嗑噔响个不停,给“遥远”的路途增添了几分烦躁。道路弯弯曲曲随着山丘延伸,从山脚到了山腰又到山顶,又从山顶到山腰再到山脚,一路上少不了颠簸摇晃,母亲一再叮嘱好好坐在座位上,注意安全不要乱动,但对于第一次“出远门”又对世界充满无限好奇的我来说,母亲的话根本成了耳旁风。我一路都不安分,一会儿扶着车窗,一会儿离开座位到前排看看车窗外的景物,看到高高低低的植物,就像严阵以待的军队,整整齐齐地并排往后飞速流走,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速体验,想象着它们都有着生命,在以自己的方式跟我道别,期待着跟我再次相遇。
那时的我对于时间的认识并没那么明显和具象,总感觉两个小时好漫长好漫长,总是一会儿就问母亲快到了吗?快到了吗?母亲的回答总是快到了,马上就到了……在快到山顶的地方,刚好可以看得到勐佑的全景,母亲提醒我说那就是我们的家勐佑了。我立刻扶好扶手定睛望去,整个小坝子被笼罩在浓浓的大雾下,厚厚云雾覆盖下的勐佑,就像仙境一般,一尘不染。第一次以俯瞰的视角看自己生长生活的地方,就看到如此美丽的一幕,我的内心里不由得升腾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激动,因为我看到浓雾笼罩下的勐佑就像一个躺在母亲怀抱的孩子,安静乖巧,让人想要疼惜。
至此我也终于明白,雾并不是从天上就下来的,而是停留在山与山之间的“云”。后来在学校上了自然课,我问老师关于雾形成的问题,老师说那是由于早晚气温差异导致水汽蒸发凝结聚合形成的,勐佑的雾是因为山与山之间的气温低湿度大,水汽不容易蒸发,所以形成厚厚的雾。
在勐佑的冬天里是很难看到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光景的,因为太阳基本上都是要到上午11点前后,等浓雾慢慢散开才悄悄露头;所以人们都是“先”于太阳出来就开始劳作了。长大后有机会到各地游览,难免被遇到的美丽风景吸引,但因为不曾割断的家乡情,总会感念家乡那一幕厚重的雾。也许因为快乐和无忧总会是我们最想、最先想起和怀念的时光,所以童年时的记忆总是最牢固和稳定地占据着我们长大后的生活,也正因为这样,现在的我无论走到哪,对雾都有种情有独钟意犹未尽的情愫,因为它让我在不同的地方还原和邂逅了我对家乡那独特的感觉,总会让我想起度过快乐童年的勐佑。
如今的家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镇化和道路交通建设的加快,慢慢地褪去了一些乡土气,多了几分现代感,但那份大家熟悉的烟火气依然浓厚,那就是勐佑人都有的春温暖、夏不热、秋凉爽、冬不冷的季节期许,如此简单、淳朴的生活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元旦我再次回到家乡,顺甸河蜿蜒曲折,静静地流淌,直到远方,只有那一塘坝的浓雾始终如一,散了又聚,聚了又散。
梦 中 的 老 房 子
最近频频梦到小时住的老房子。想起老房子,一个普通的云南南方小院,两间卧房一间堂屋,主房侧边又附着一间生火做饭的灶房,都分割为两层,四周被围墙围住,院脚有个父亲用废弃青砖砌的花台,说是花台却是没有种过一棵花,而是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果树,有杏子、树番茄、桑葚、葡萄、番石榴。
父亲随手在墙外插上了几株薄荷,没过多久就茂盛了起来,嫩油油的一片,夏天摘些回来,拌上母亲自制的米醋,那是我的童年里最好的消暑佳品。
我祖上世代靠农业谋生,自然是黏在土地上的,向泥土讨生活的人不能老是移动,能将我们固定下来的便是房子。房子成了黏在地上的最好例证,黄土墙木房梁灰瓦房,就地取材,它是从我们赖以活命的地里“长”出来的,浑身都是土里土气的。
一座房子就是一个家,人间烟火赋予了它人性的温度,有了这种温度才是家,是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寄托,我们像爱护身体一样爱护着我们的家。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以家的名义“生与斯,死于斯”。那是有赖于泥土的生活,像植物一般在地下生根,根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在悠长的岁月中,从容地生活劳作,根越长越深,心也就越久越稳。
记忆就像剪辑好的胶片电影,每一帧都是一个脚步,构成一幅幅人生轨迹的图景。我们依靠那些有时间意义的图景来筛选要保存的帧格。记忆中的老房子就像父亲的后背一样结实厚重,老房子里那些弥漫的烟火已经成了我骨子里灵魂中的一部分,是我要保存的帧格。
春天的第一只燕子来啦!一年就这样在万象更新中启幕。燕子在我家土房子的房梁上垒土搭窝,父亲撕下废纸箱一个面板垫在下面,接燕子的粪便,有时候我嫌它们太吵太脏,我就想赶它们走,父亲说不能赶它们走。我问为什么?父亲说,燕子是益鸟,是我们家的好朋友,燕子选窝,不是随便选的,它也会看人的,友好能够为它们遮风避雨,适合的人家它才会来,它们现在来了我们家,说明它喜欢我家呢。
父亲还说,无论在哪里看到它们千万不要伤害它们,也不要捅它们的窝,不然会遇到惩罚的。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的话不用意志就能够影响我在生活上的任何决定,因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由此尊听父亲的教诲,从未敢做出对像燕子一样弱于我的动物的过分的事情来。
时令到了立夏。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跟着最后一阵春风飘向了夏天。立夏这天,父亲都会煮一锅腊肉鳝鱼汤,汤里放上很多大蒜头,在土灶上用柴火熬煮一下午作为晚餐的主菜,香喷喷的。可能父亲觉得我已经长得够大了,有一年立夏,在太阳下山前,父亲用一只小桶装满灶灰,让姐姐和我绕着我们家围墙的脚根一圈撒上薄薄的一层灶灰。父亲叮嘱说灰圈的首尾一定要接满,中间是不可以间断的,一旦断开了就会有缺口,我们的家就“锁不住”了,就会危险,你别小看了,这一圈灶灰就像孙悟空要去千里之外化缘时用金箍棒给唐僧画的保护圈一样能够保证我们一年的安全呢。
我又问为什么?父亲一脸严肃地说,小孩子家的别问那么多,先去做就是了。我和姐姐将信将疑地提起装满灶灰的小桶开始去撒了,但直到“完成任务”我们都还弄不明白危险将从何而来。在夕阳最后一抹余晖快要从天边消逝的时候,父亲 “吃饭”一声令下,我们便开始享用美味的晚餐,作为进入夏天的仪式。
有些传统的习俗在大人之间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在小孩面前却像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多解释几句。但童年的好奇心就像一艘未知航向的宇宙飞船,只要启动,那些如星辰般新奇的事物,足够我花所有的时间去弄明白。关于撒灶灰的事,我忍不住再问父亲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夏天来了大蛇开始频繁活动,我们家挨着田边,撒一圈灶灰可以防止蛇进入我们的家里,而在立夏这天多吃大蒜头,作为农民的我们上山下田就不会遇到蛇,如此听来灰圈和大蒜简直就有“金钟罩铁布衫”一般的威力呢。2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都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真的有用,但是它已成为我童年记忆图景中的一个帧格了。
“金钟罩铁布衫”再有威力,毕竟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虽然父亲的解释让我接受了,但同时也让我难受起来。我开始怀疑我家附近,就在我家围墙外就有一条大蛇。这种害怕,在奶奶给我讲一个大蛇吞猪的故事之后,变得无以复加。奶奶说:在隔壁村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情,一条大蛇出来找食物,爬到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出门干活去了,看到一头猪就张开盆子大的口,一口就把那头猪吞进去了,因为猪太大,那条蛇消化不了,还没爬出那家人外就撑死了,那户人家回来把蛇肚子划开,发现了那头猪……这成了我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
从此,每当天黑我总是难以入睡,因为房子就建在田边,周围当时还没有一家邻居,更要命的是房子的一层和二层之间完全没有任何隔音效果。我家成了老鼠们的“夜场”,天一黑它们就始在楼板上上蹿下跳追逐打闹,总是不知疲倦地彻夜狂欢,我感觉整个楼板就要被它们攻陷了,仿佛闭上眼睛它们就掉下来了,害怕急了。
黑是夜晚的代名词,同时也是恐怖的近义词。为了觅食,蛇不光会吞下一头活猪,还会钻进老鼠洞里,因此每当黑夜,我还另外一个担心,不敢往墙上看,生怕大蛇就往墙缝里钻出来。理智上,我知道这只是我脑海里想象出来的事,情绪上,我却不得不相信那是真的。一面希望大蛇来把老鼠们捉了去吃,一面又怕它来把我也吃了。一想到这里我就会害怕得裹紧被子抖作一团,直发冷汗,双眼紧闭却头脑清醒。终于,我在一只猫的嚎叫声中崩溃大哭,于是半夜总是哭着去敲父母的房门,母亲说怎么了,我都是撇着语气娇声娇气地哭着鼻子说,我睡不着,我害怕,我要来你们睡。
有毁童年的恐怖阴影,也有美好的记忆图景。
秋天,番石榴熟透了。与生俱来的恐高使得我不会爬树,我生怕不经意间就踩断了树枝掉落下来,事实证明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直到今天我甚至都没有爬上过任何一棵树的树腰。看着小玩伴们爬到树上去摘果子尽情地吃着完好又美味的果子,我却只能拿着棍子在树下揣,把果子揣得满目疮痍,或是掉在地下不摔个粉身碎骨也是皮开肉绽的,我总是只有羡慕的份。虽然不会爬树至今仍是我人生中的一大遗憾,但那些揣坏的果子确是我永远的回味。
生产和收获都是间接季候性的,吃饭却是终年的事。像我的父辈这样生活在乡村的人,有了泥土就能够自食其力,但也得靠天吃饭,自然会特别关心每件与季节气候变化有关的事,因为完全得据此来开展农作活动,在农忙时节,很短的时间里,不能提早也不能延迟,丝毫都不能马虎。
我家围墙外面就是成片的稻田,围墙外的打谷声此起彼伏,声声振撤。一个木制的四方形的大海簸,百十来斤重,平时用来储备粮食,收稻谷时用来打谷子。打谷子非常辛苦的,太阳的热辣并不会因为人们的辛苦就减弱半分,父亲热得脱掉上衣,本来黝黑的皮肤晒得更黑了,只有肩上两个挑谷子时留下磨蜕皮的挑担痕是白的。
没有机械的年代,打谷子是需要人工配合密切协作的活计,割的割,打的打,挑的挑,捆的捆,需要有很好的分工。只见人们七手八脚割完稻谷,使尽全身力气把稻谷打掉抖落进大海簸,几根抖落干净的稻草马上被捆成了一把,几把又束成了一扎,不一会儿田里就只剩下一个个扎紧脑袋半摊开的稻草人,干透后的稻草人则挨个从脚开始堆叠起来,极目远望,一个个草堆像是蒙古包,像极了梵高画笔下的《麦田》。
冬天到了,父亲的活也少了一些,终于轮到母亲大显身手了。冬至节,母亲前一天就了泡好的大米,经过蒸熟、分散、冷却再蒸熟几番折腾,拿到机器里碾碎成絮状,再经过道道揉压按滚的工序,便成一锤饵块粑粑了。因为我爱吃饵块粑粑,再怎么麻烦母亲不会落下不做的。
空闲时,父亲会给我讲我已听过很多遍的故事,有那些他上学用功、18岁出去当兵值得他自豪的事,也有藏在心底愧疚和遗憾的事。父亲总是有种“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般的无奈,但他都试图以此来鼓励我要好好学习。他告诉我人生曲折在所难免,认准了用心努力去做好就行。长大后才明白,自我完善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没有尽善尽美的,真诚和坦荡是做好一切的前提。
时光就这样在老房子里流过。回忆是一种朦胧又讲不清楚的过程,是一种本能,在如今物质充沛的城市生活里,那些物质匮乏充满泥土气息的日子只能通过回忆来寻找。那是我出生直到25岁住的老房子,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一幕幕琐碎零星的片段拼凑出我在老房子里成长的岁月,一阵阵涌上心头,或是快乐,或是痛苦的感受,如今都成了印在我心底的一座雕塑。(作者:段珊珊)
|